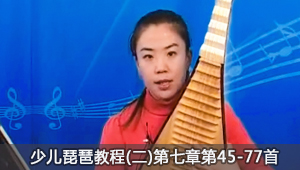淺析“琵琶”于《琵琶行》戲曲改編作品中作用的變化(一)
導語: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琵琶行》向來被譽為唐詩之翹楚,世代傳誦不絕,元明清時期,更被作為戲曲題材加以改編,并搬上舞臺。而“琵琶”這一中心道具在《琵琶行》的戲曲改編作品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劇作的故事模式,主題中心的不同,又使得這中心道具的功效,包含的意蘊,表達的情緒,情感的張力也隨之發生了不同的變化。 就作品的故事模式來看,馬致遠的《青衫淚》和顧大典的《青衫記》是屬于同一體系的,講述白居易與妓女裴興奴交往,而后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裴興奴被茶商騙婚,也帶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聞興奴琵琶聲,二人重逢。最后白居易復官,與裴興奴奉旨成婚。而《青衫記》除卻描寫白裴的愛情,又增加了白妾樊素、小蠻與裴興奴之間的糾葛,情節趨于復雜;同時更以一件青衫作為貫穿全劇的中心線索,借此大做文章。 而蔣士銓的《四弦秋》則完全摒棄了《青衫淚》和《青衫記》的愛情故事模式,嚴格的按《琵琶行》詩作原意,參照了《新唐書》元和九年、十年史實及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所提供的材料,淡化了男女之情,以琵琶女作為貫穿全劇的核心人物,通過對琵琶女的悲涼身世的感嘆表達了封建社會中眾多胸懷不凡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琵琶行》向來被譽為唐詩之翹楚,世代傳誦不絕,元明清時期,更被作為戲曲題材加以改編,并搬上舞臺。而“琵琶”這一中心道具在《琵琶行》的戲曲改編作品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劇作的故事模式,主題中心的不同,又使得這中心道具的功效,包含的意蘊,表達的情緒,情感的張力也隨之發生了不同的變化。
就作品的故事模式來看,馬致遠的《青衫淚》和顧大典的《青衫記》是屬于同一體系的,講述白居易與妓女裴興奴交往,而后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裴興奴被茶商騙婚,也帶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聞興奴琵琶聲,二人重逢。最后白居易復官,與裴興奴奉旨成婚。而《青衫記》除卻描寫白裴的愛情,又增加了白妾樊素、小蠻與裴興奴之間的糾葛,情節趨于復雜;同時更以一件青衫作為貫穿全劇的中心線索,借此大做文章。
而蔣士銓的《四弦秋》則完全摒棄了《青衫淚》和《青衫記》的愛情故事模式,嚴格的按《琵琶行》詩作原意,參照了《新唐書》元和九年、十年史實及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所提供的材料,淡化了男女之情,以琵琶女作為貫穿全劇的核心人物,通過對琵琶女的悲涼身世的感嘆表達了封建社會中眾多胸懷不凡而又壯志難酬的知識分子的郁悶和悲憤,突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主題。
正是因為故事模式的不同,反映主題的不同,使得“琵琶”這一中心道具,在這三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包含的意蘊,也有所不同。
一、初識
在《青衫淚》、《青衫記》和《四弦秋》的伊始,“琵琶”便承擔了促成白居易與琵琶女相識的重要媒介。
在《青衫淚》和《青衫記》中,妓女裴興奴的名聞京城的高超的琵琶技藝,是吸引白居易前往拜訪的重要因素,“聽的人說。這教坊司有個裴媽媽家一個女兒。小字興奴,好生聰明,尤善琵琶,是這京師出名的角妓。咱三人同訪一遭去來。”而正是這一訪,促成了白裴二人的愛情,也引發了日后二人之間種種的悲歡離合。
在《四弦秋》中,白居易月夜行船,忽聞琵琶聲,引發萬千感慨,進而邀請琵琶女上船一敘。而此“敘”完全不同于《青衫淚》、《青衫記》中帶有獵艷性質的“訪”,這是白居易由京官被貶為江州司馬后,于苦悶憤恨之時,聞得似曾相識且同懷郁悶之音的琵琶聲,同病相憐之情油然而生,故而極為自然的產生與知音相見之心,“(生)呀!這琵琶音調錚錚然有京都之聲,左右,可去小船中,問是何人彈唱!”
由上可見,在三部作品中,“琵琶”同樣承擔了白居易與琵琶女的“初識”工具的作用,但卻有本質的差別。在《青衫淚》和《青衫記》中,“琵琶”促成的是愛情之識;在《四弦秋》中,“琵琶”促成的是知音之會。不論從格調雅俗來看,還是從遵從《琵琶行》詩作原意上看,《四弦秋》都是更勝一籌。
二、抒懷
在《琵琶行》一詩中,“琵琶”明顯的起到了抒情遣懷的作用,而這一用途,在其戲曲改編的作品中,均加以沿用,只是由于故事主題的不同,而使得以琵琶抒懷的內容,情感力度也有了變化。
相關內容
- 如何避免練習鋼琴時的不良習慣 2014-11-24
- 如何防止過度練習產生的傷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對攝像機你該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樂學院琵琶考級演奏文憑級教材目錄2014-11-17
- 中央音樂學院琵琶考級9級教材目錄2014-11-17
- 中央音樂學院琵琶考級8級教材目錄2014-11-17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