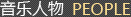民歌教學和系統研究的開拓者——憶耿生廉
錄入時間:2012/2/20 14:30:00 來 源:中音在線 [音樂教程]
此外,在民歌的教學和研究中,耿先生歷來重視對民歌的田野調查工作。僅據《耿生廉音樂活動實錄》中的不完全統計,耿先生在1953年—1985年的30多年間,就進行了民歌的田野調查工作20余次;扣除“文革”時期的間斷,其田野工作的頻度在每年一次以上。在我準備碩士學位論文寫作時,耿先生要求我在動筆之前,首先要到民歌產生和流傳地進行較為長期的田野工作。我遂于1990年夏天到四川省平武縣和南坪縣(今九寨溝縣),為調查白馬藏族民歌做了兩個月田野工作,共搜集到百余首白馬民歌,并對白馬民歌的生存背景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據此形成約10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四川白馬藏族民歌的描述與解釋》。
課程內容的充實豐滿。就我自己的體驗,耿先生上民歌課時,對于民歌曲目資料不僅是毫不費力地信手拈來,而且對這些曲目大多能進行風格準確的范唱。耿先生在其授課中,對于他提出的每一個理論觀點,都會列舉出并親自范唱許多民歌曲目予以說明和佐證,使學生在課堂學習中能夠打通感性和理性之間的障礙,獲得立體生動的感知與認知,并因此而對授課內容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對于目前高校藝術理論課程講授中,普遍存在的重形式輕內容、重理性輕感性、重文本輕體驗、重理論輕事實的現狀,耿先生的教學顯示出其更大的合理性。
在民歌的理論研究方面,耿先生也有著相當大的建樹。早在1979年,耿先生就提出了“民歌的家族”這一概念,并對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和論證。他指出,“例如在我國西北地區有一個《攬工詞》家族,它的變體不下數十種,廣泛流行于隴東、陜北、山西、青海和河北西部的廣大地區。”耿先生對“民歌家族”概念的提出及其相關研究,比國內學者的同類研究早了若干年,這表明他在上世紀70年代的民歌研究領域中,已經率先和自覺地涉入了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的研究范疇。
在民歌研究的田野工作方面,耿先生在發表于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對中國民歌“集成”工作,提出了要高度重視民歌的“收集”工作的意見。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第三條意見:“要有比較全面的民歌概述、歌種釋文和歌曲注釋。把所有的歌種和歌曲生成的環境、歷史背景、社會基礎、分布狀況和活動的時間、場合及其變異、發展的情況等都通過文字反映出來。這也正是《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和過去出版的民歌集子的不同。”這個意見中體現出來的觀念,實質上就是音樂人類學“將音樂事象放到其文化背景上去觀察和研究”的基本方法論。耿先生在20多年前提出的這一意見,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和音樂人類學方法論的自覺性。
在對民歌的文化功能的認識方面,耿生廉先生在寫作于1984年的論文《論民歌的社會功能》中,在中國大陸音樂學界比較早地提出了民歌的文化功能研究問題,并梳理歸納出中國民歌的五大文化功能:抒表功能、娛樂功能、教育功能、戰斗功能、實用功能;并將民歌的實用功能細分為“勞動助手”、“婚戀媒介”、“民俗儀禮”、“生產/生活顧問”,以及“調節糾紛”、“以歌代信”等。相對于此前中國大陸數十年來占主流地位的音樂功能“教化說”、“審美說”和“娛樂說”來說,耿先生的這一認識表明,他在當時即已自覺和明確地將“民歌”一類人類音樂事象,看做一種功用相當復雜的文化事象(cultural event),而非一種功用相對單純的“藝術事象”(art event)。在今天來看,這篇論文中的民歌功能認識盡管還不甚全面,但其在當時已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并與當時開始在中國大陸興起的音樂人類學學科的音樂觀,可謂不謀而合。
上述種種,遠不足以全面完整認識耿生廉先生一生之中,對中國民歌的教學與研究事業作出的貢獻。筆者僅僅是冀圖通過此文,對這位為中國民歌文化的傳承奉獻了一生的老人,表達一個學生的敬愛與思念之情。(作者何曉兵,現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編輯/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