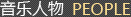民歌教學和系統研究的開拓者——憶耿生廉
錄入時間:2012/2/20 14:30:00 來 源:中音在線 [音樂教程]
我的導師耿生廉先生,于2011年5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歲。6月19日,中國音樂學院舉行了耿先生的追思暨學術研討會,紀念這位中國高校民歌教學和系統研究的開拓者。
耿先生是新中國培養的以中國民歌作為主要學習和研究對象的第一代大學生。他1927年生于山西大同的一個郵局職員家庭,從童年學習“吹皮皮”(樹葉)開始,涉足了終其一生的音樂生涯,小學時在學校樂隊吹奏笙和笛子,在蘊藏豐富的晉北傳統民間音樂環境中,完成了自己音樂人生的啟蒙。1949年夏秋之時,先生為繼續求學從大同來到北京,報考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先后師從過馬可、劉熾、鐘敬文、張肖虎、陳田鶴、老志誠、焦菊隱、沈湘等一代學者和名師,其中給予耿先生在學術上和文化價值觀方面影響最大的,是教授民間音樂課程的馬可和劉熾先生。由于學習的認真刻苦,以及對中國傳統民歌的強烈興趣,耿先生于1953年畢業后留校任教,除了擔任系秘書之外,由理論教研室主任張肖虎先生安排獨立教授民歌課程。
由于當時的中國高校音樂教育基本是一個歐化的格局,大學的民歌課程尚處于斬茅初創之期,耿先生回憶這段時期曾說:“除了馬可和劉熾二位老師編印的一本薄薄的民歌講義,和一本僅有二三十首民歌的曲譜資料外,別的有關民歌的資料什么都沒有。”這門課程需要的教材、曲譜、錄音、文字資料和教學大綱等等,都要從零開始積累創建。經過一年多的奔波于圖書館、書店、民族音樂研究機構、廣播電臺等機構搜集資料,在張肖虎、劉熾和鐘敬文先生的大力幫助下,耿先生終于在1954年的春季,于北師大音樂系獨立開設了民歌課,并于是年秋季編寫出國內高校第一套系統的民歌課程講義。這是新中國的高校中開設的第一批民歌課程,也是中國民歌之系統理論研究的發軔之時;作為中國高校民歌教學和研究的先行者,耿先生于此領域艱難舉步時,年僅27歲。
1993年從中國音樂學院退休之后,耿先生仍承擔著學校各學歷層次學生的民歌理論教學,其民歌教學生涯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其民歌研究工作則幾乎持續了一生。在半個多世紀的民歌教學和研究生涯中,耿先生共編寫出33套民歌教材,這些教材被國內很多高校的藝術專業或課程所引用;記錄了145本《民歌札記》與《民歌隨筆》,擔任過《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的特約編審員、《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北京卷》副主編。耿先生一生培養了大量從事中國民歌研究和表演的本科生與研究生,為中國民歌和民間音樂的教育傳承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與中國民歌之間,是一種終生相伴、血肉相連的關系。按先生自己的說法,“我這輩子就做了一件事——學習、整理、研究、教授民歌。民歌與我,永不分離!”
我與耿先生的人生交集,開始于1985年春夏之交的云南。那是我在西南師范大學音樂系任教的第二個年頭,代表學校到云南昆明招生,恰逢耿先生應云南藝術學院之邀在那里講學。在聽了耿先生的民歌講座之后,我向先生表達了想報考他的研究生的想法,當時即獲得先生的欣然允諾。1988年,在耿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之下,我考入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成為耿先生指導下的、以中國民歌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就我在隨后3年中隨先生學習中國民歌的體會,先生的民歌教學體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特點:
對音樂價值觀的正確把握。1979年,正值國門初開,歐美音樂和港臺流行音樂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大陸學界和社會各界對外來音樂的好奇與崇拜之心勃然興起的時候,耿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清醒而明確地提出,“我們也要向外國音樂學習、借鑒。但學習的目的是豐富我們的音樂藝術,要以我為主,‘洋為中用’。絕不能以西代中,取而代之。”并在該文中以若干的實例,對中國歌劇、舞劇音樂和創作歌曲與民歌的源流關系,予以了令人信服的論證。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在民歌教學中,耿先生一貫提倡民歌的學習——不管是理論還是表演專業的學生,都要首先學習民歌的演唱。先生對民歌演唱的要求是:在演唱中一定要充分地投入情感,不能像“視唱”練耳一樣唱民歌;要盡可能多地積累習唱的民歌曲目,而不能會唱幾首就自詡了解中國民歌;要準確地把握不同民族或地區的民歌的特殊風格;一定要用當地方言(而不是普通話)演唱民歌,并提倡用少數民族語言演唱少數民族民歌;除此之外,還要盡可能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民歌流傳地的文化背景。
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耿先生總結出一套系統的和行之有效的民歌教學方法,并稱之為“民歌教學基本六大法門”:“聽(錄音或老師唱)、看(錄像或現場)、唱(模唱)、分析(討論和寫文章)、記(記譜)、模寫(給歌詞,按風格寫旋律)”。耿先生認為,在這“六大法門”中,“唱”是最主要的,并對學生影響最大。而且,“唱”絕不能停止在“視唱”上,因為民歌的完整性和感情風格,僅僅依靠譜面是感受不到的,原則上應該貼近原生風格。“六大法門”的提出,對于國內藝術類高校(專業)民歌課教學方法體系的形成,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