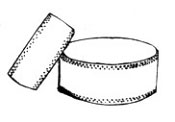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梁祝》的原創者應該是農民伯伯(二)
導語: 文/本報記者 鄧瓊實習生 陳培娜圖/本報記者 鄧勃 人物檔案 何占豪,1933年生于浙江諸暨,中國杰出音樂家,現任中國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中國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17歲進入浙江省文工團,1952年轉入浙江省越劇團樂隊,1957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先后在管弦系、作曲系就讀。1959年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期間與同學陳鋼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婦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錄音版本最多的中國管弦樂曲。 何占豪憶及50年前創作《梁祝》的點滴,一再強調《梁祝》是集體創作的結晶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次公演,俞麗拿擔任小提琴獨奏。這支中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響音
高手點撥
沒動筆已覺害怕
唱越劇找回信心
羊城晚報:那為什么您說寫的過程中,一動筆就覺得害怕?
何占豪:我還沒動筆就害怕了。我以為領導說要寫的話,肯定會有作曲的人去寫,我們只是提供幫助嘛,我們又不是作曲專業的。所以當劉品在實驗小組會上說要我跟丁芷諾(小組的另一成員,我的同班同學)寫,我就傻了,馬上就說不行!我肚子里的“貨色”已經被掏空了,不可能寫得了!當時是夸海口,一腔熱情,我很愿意寫,但本事沒有!
晚上,劉品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叫我一段段唱越劇,還說你沒被掏空啊!可我說:“這是越劇啊,又不是小提琴曲!”這個時候他講了一句關鍵的話:“你不要以為貝多芬、莫扎特頭腦里的音樂是天生的,他們的音樂也是從當時的民間音樂中提煉出來的。”這句話把我點清楚了!對啊,這些民間音樂也可以成為小提琴曲子的哦!這下我思想就通了,從“要我寫”變成了“我要寫”。
無名英雄
同窗作貢獻讓榮譽
請她補名她謝絕了
羊城晚報:從這時候開始,陳鋼先生就加入了嗎?
何占豪:還沒有。當時劉品提出“既要有沖天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頭腦”,我們有民間音樂素材、有沖天干勁,但是還缺什么呢?缺配器的知識,大的樂隊、銅管、木管樂器的組織技巧都沒有,我們只會拉小提琴。寫交響樂需要有技術平臺啊!丁芷諾是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先生的女兒,就推薦了丁先生的作曲系學生陳鋼。然后我去跟陳鋼談,把我們的偉大理想講了一遍,可是陳鋼沒有答應我們,他當時的理由是要寫畢業作品,沒有時間做。其實是他不大看得起我們這幫業余選手———這個想法他還是在50年之后、前不久才透露給我聽的!哈哈!他當時不答應,我們就自力更生。我跟丁芷諾構思,什么“三載同窗”、“草橋結拜”、“樓臺會”等等,然后自己寫主題。前三個月,從1958年11月接到任務到1959年2月份做了這些基礎性工作。
另一方面,劉品把我們的情況介紹給丁善德,丁善德副院長決定要陳鋼參加實驗小組的創作。他就服從領導的決定同意和我們合作了。這是在1959年2月,我們歡天喜地,覺得實驗小組的第一首大型樂曲有希望了。這時候丁芷諾很謙虛,就說他來了,我可以退出了。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梁祝》的前期創作中,丁芷諾也作了貢獻?
何占豪:在紀念《梁祝》問世50周年的時候,我要特別說清楚這段歷史。丁芷諾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前期,而且后來我與陳鋼合作過程中,他把總譜遺失、要趕時間重新編配的時候,又是丁芷諾來幫忙,加快進度,“三載同窗”那一段小快板基本上就是她配器的。你看,丁芷諾參加了第一階段的創意和共同構思,又參加了第二階段的配器,做了很多工作,實際上完全應該可以把名字列到作者里面的。但當時署名及其排位都由領導決定,就寫了“何占豪、陳鋼”。丁芷諾現在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她一直甘當無名英雄。我曾經提議補上她的名字,但她謝絕了,怕被人誤解。但在我心目中,她是當時年輕人“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的一個典型。
險留遺憾
不想迷信抹掉“化蝶”
領導聽了哈哈大笑
羊城晚報:聽說《梁祝》這曲子差一點就沒有后面經典的“化蝶”部分?
何占豪:哈哈,是有這么回事。《梁祝》作品出來后,我們向領導進行匯報演出,匯報時我拉小提琴,陳鋼彈鋼琴。整部曲子拉到《哭靈投墳》就結束了,音樂戛然而止。領導有些納悶:“沒有了嗎?”我倆回答:“沒有了!”“《梁祝》怎么能沒有‘化蝶’呢?”我不假思索回答:“沒有《化蝶》,化蝶是迷信!我們新中國青年是不迷信的!”話音剛落,在座的領導都笑了,但還是指示要加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最美的“化蝶”!
這下子可難倒了我,所有的素材也都用完了,哪還能《化蝶》?多虧我突然想起,五六年前,在杭州時曾看過蘇州昆劇團《梁祝》的演出,當時《化蝶》的那段笛子獨奏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后來我跑遍了全上海,終于在一家新華書店找到了相關的材料,所以最后的《化蝶》是我根據這段昆曲,又加上著名琴師賀仁忠老師編曲的越劇《白蛇傳》中的《斷橋》部分,再加上哭腔完成的。
羊城晚報:難怪行內人都說,光看譜子不能理解《梁祝》的中國神韻?
何占豪:對,這是事實。我從越劇團帶來一種民族化的小提琴演奏方法,我也不是天生就會的,而是在賀仁忠老先生的指點下,還有我自己跟著越劇演員的唱腔進行模仿才形成的。到了實驗小組里,丁芷諾等人對這些演奏手法進行了歸納、提煉和規范化了,比如向上滑動叫上滑音,還有磨音就是來回滑動等等。所以準確地講,這個《梁祝》演奏的特殊風格是集體創作勞動的成果,由俞麗拿來體現。
意外成名
第一天演出結束
第二天下鄉勞動
羊城晚報:很多作曲家一生都沒有看到自己的作品成功,而您和陳鋼卻是從一出手就受益于這支曲子,您覺得這是人生的大幸運嗎?
何占豪:當年只有一個人,就是劉品講過,我們很可能會在中國音樂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但我那時候絕對不會想到名留青史。就算那天演出完了,人家都來祝賀,我卻一點也不興奮,因為當時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本來只能挑五十斤的,后來加到一百斤、一百五十斤!觀眾一鼓掌,我覺得總算完成了任務,輕松了,領導不用找我了!我第二天就下鄉去勞動了。
后來我收到了好多來信。當時寫信的人并不是說“我怎么崇拜你”之類,而是這么說:“謝謝你,使我聽懂了音樂!”我們原來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廣大勞動人民聽懂,所以人家這樣說,我心里很安慰,覺得這條路子走對了。于是我一直走這條路,不管風吹浪打,不管什么新潮音樂,我自巋然不動。
羊城晚報:那您的這種風格有沒有受到過非議
何占豪:當然有過。有一次在香港,記者很尖銳地說:“何先生,你的作品有不少人很喜歡,但有很多人認為你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陽春白雪。你自己怎么看?”我說,人家評論我是下里巴人我非常高興,我寫東西就是為了使下里巴人、廣大群眾都聽懂。但我反問一句,有沒有哪一個作曲家說,我的曲子越少人聽懂越好?沒有吧。我的聽眾里有我們的外交部長、總理,還有外國的總統、皇帝都來聽《梁祝》,那么他們是不是下里巴人?如果他們是,那么大家全體都是下里巴人。我的路子就是追求雅俗共賞。
羊城晚報:香港評最受聽眾歡迎的十首交響音樂作品,除了貝多芬第九與第五交響樂、柴可夫斯基“天鵝湖”等九首外國名曲外,《梁祝》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作品。您怎么看待《梁祝》在音樂史上的地位?
何占豪:這個我不敢說。但是這個曲子是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交響音樂作品,它用中國人民的音樂語言,表達了一個中國民間故事。為什么現在要這么隆重來紀念其誕生50周年?也許就在于它讓廣大勞動群眾聽懂了。
相關內容
- 音樂課變“音樂會” 巴蜀小學以演代評2014-12-3
- 廣東省第六屆群眾音樂舞蹈花會在肇慶決賽2014-12-3
- 海口一中舉行“心懷感恩·與愛同行”愛心音樂會2014-12-3
- 徐晶晶感恩獨唱 音樂旅程華麗啟航2014-12-3
- 趙季平專場音樂會明晚鄭州奏響2014-12-2
- 兩岸專家在福州研討音樂學術現狀2014-12-2
熱點文章
熱門標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