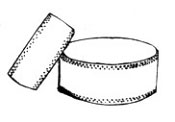上海交響樂團(tuán)復(fù)工演出 指揮家余隆在忙什么
上海交響樂團(tuán)復(fù)工演出 指揮家余隆在忙什么

聽說上海交響樂團(tuán)即將復(fù)工演出,海外音樂家紛紛向音樂總監(jiān)余隆發(fā)信道賀,“真為你們開心!生活終于回來了,恭喜上海的音樂家們,恭喜上海的觀眾們!”
道賀名單里包括大提琴家戈蒂埃·卡普松、小提琴家雷諾·卡普松、指揮家丹尼爾·哈丁、指揮家夏爾·迪圖瓦等大牌藝術(shù)家,在很多國家的劇場(chǎng)還在關(guān)門、演出還遙遙無期時(shí),國際交響勁旅上交的復(fù)工,為古典樂壇點(diǎn)燃了希望、打了強(qiáng)心劑。
“他們很關(guān)注上交,很羨慕我們復(fù)工,是真心為我們喝彩。”余隆感慨,“難以想象,從三月到六月,全球音樂家集體失業(yè),所有音樂會(huì)都不開了,所有歌劇都不演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不僅僅是一場(chǎng)音樂,也是上海給世界的信心。”
6月13日晚,面對(duì)361位觀眾,余隆將率領(lǐng)上交獻(xiàn)演格里格《索爾維格之歌》、理查·施特勞斯《最后四首歌》、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這是上交所有聲部音樂家在鼠年以來的首次齊聚,也是疫情以來上交首批售票演出之一。
“既致敬逝者,也憧憬未來。”這是余隆對(duì)這場(chǎng)音樂會(huì)的設(shè)計(jì),曲目也經(jīng)過了特別的調(diào)整和挑選:上半場(chǎng)致敬逝者、最美逆行者,以及環(huán)衛(wèi)、交通、警察等一線工作者;下半場(chǎng),在貝多芬的“田園”里看到對(duì)希望、對(duì)未來、對(duì)生命的憧憬,貝多芬已經(jīng)不僅僅屬于德國,而是全人類的精神遺產(chǎn)、精神象征。
6月28日,上交2019-20音樂季閉幕音樂會(huì),余隆還要帶團(tuán)演繹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堂·吉訶德》,“人有時(shí)候需要堂·吉訶德那種精神,一根筋,專注做一件事,才能完成一些事,才能放棄很多虛無縹緲。”余隆笑說。
余隆上一次在舞臺(tái)上的重要亮相,還是1月底率紐約愛樂樂團(tuán)舉辦“新春音樂會(huì)”,那時(shí)候,正是中國疫情最兇猛的時(shí)候。
很多人勸余隆留在國外,但在2月8日這一天,他堅(jiān)持回了國。
“所有音樂家都在國內(nèi),我是這個(gè)家庭的一員,我要和他們?cè)谝黄稹H绻以谕饷妫覍?duì)不起他們。”責(zé)任感促使余隆回了國,回過頭看,他感慨,“回來是很正確的,你要對(duì)你的城市、你的國家有高度的信任,你要為你的城市、你的國家感到自豪。”
因?yàn)橐咔椋嗦〗衲暝诿绹⒂⒎▏⑷鹗俊W地利、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的音樂會(huì)都取消了。一直以忙碌著稱的余隆停了下來,然而閉關(guān)期間,他也沒閑著。
除了指揮家的頭銜,余隆還有一個(gè)身份是藝術(shù)管理者。也因此,他每天都要和上交,和歐美的經(jīng)紀(jì)公司、樂團(tuán)、藝術(shù)家開電話會(huì)議,調(diào)整節(jié)目策劃、調(diào)整演出檔期。
“上交建立了一個(gè)非常完整的系統(tǒng),所有工作都在有序進(jìn)行著。”余隆透露,上交的工作計(jì)劃已經(jīng)排到了2023年,不久便會(huì)公布2020-2021年度音樂季,9月開始的新音樂季完全根據(jù)國內(nèi)外疫情設(shè)計(jì),非常嚴(yán)謹(jǐn),以減少無謂的取消和推遲。
在嚴(yán)防境外疫情輸入的當(dāng)下,今年年底以前,余隆對(duì)海外演出項(xiàng)目進(jìn)中國持謹(jǐn)慎態(tài)度。在他看來,這也給了中國音樂、中國音樂家一個(gè)機(jī)會(huì),做一次規(guī)模空前且高質(zhì)量的“大檢閱”,“這在二十年前是很難想象的,你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開放的生命力有多大,給這個(gè)時(shí)代帶來多少創(chuàng)造力,很多中國音樂家都是這個(gè)時(shí)代出來的,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一代人。”
疫情期間,余隆也看到了線上音樂會(huì)的如火如荼,在他看來,高科技為藝術(shù)插上了翅膀,帶動(dòng)了信息的傳播,但不會(huì)真正取代線下的人文交流。
“線上音樂會(huì)你幾乎分不出樂團(tuán)的好壞,因?yàn)榭梢灾谱鳎涣鳂穲F(tuán)和六流樂團(tuán)都在線上播,你會(huì)覺得沒區(qū)別。但你把做事情的規(guī)矩破壞掉了,一流樂團(tuán)背后有大量工作,有仔細(xì)精準(zhǔn)的排練,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余隆比喻,就像看電影,在線上看和在電影院看,感覺肯定不一樣,“藝術(shù)的沖擊力是要夸張的,但那種沖擊力,你在小小的電腦、小小的手機(jī)上感受不到。”“藝術(shù)要直抵人心,一定要人和人面對(duì)面交流,要人和人有情感的撞擊。”
2003年非典最嚴(yán)重時(shí),余隆帶著大提琴家王健和東京愛樂樂團(tuán)在上海美琪大戲院演出了一場(chǎng),轟動(dòng)一時(shí)。非典結(jié)束后,中國第一場(chǎng)現(xiàn)場(chǎng)音樂會(huì)也是在余隆的帶領(lǐng)下恢復(fù),在廣州。
“這次疫情更嚴(yán)重,是全球性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都卷入其中,顯露無疑。”前不久,余隆和大提琴家馬友友深聊了一次。馬友友感覺,舞臺(tái)和觀眾之間的那種親密關(guān)系很難再回來,因?yàn)橐咔樽寚抑g、城市之間、家庭之間、人與人之間都有了距離,所有距離都在拉開。“這是事實(shí)。”余隆坦誠,真正能把大家重新聚攏在一起的,也是藝術(shù),因?yàn)槿撕腿丝梢栽谒囆g(shù)里互相被感動(dòng)。
除了打不完的電話會(huì)議、忙不完的工作,疫情期間,余隆也給自己留了一點(diǎn)時(shí)間。
他開始精進(jìn)英語、法語,以及自己在德國留學(xué)期間學(xué)的德語;他看了一堆書,比如麥家的《人生海海》、劉慈欣的《三體》;他開始騎自行車上班,見到紅燈就老老實(shí)實(shí)停下來;前不久,他還給自己買了一輛重型摩托,偶爾就要在北京街頭遛一圈,倒在地上要六個(gè)人才能扶起來,騎著摩托車的余隆戴著一幅墨鏡,霸氣外露的街拍很快刷屏了朋友圈。
“你們采訪過張文宏嗎?他這個(gè)人說話很來勁的,采訪他比采訪我有意思多了。”采訪中途,余隆突然提到了年度偶像“張爸”,“音樂會(huì)什么時(shí)候恢復(fù)正常,你們要問他。你們可以隔空喊一下,請(qǐng)張文宏來聽我們的音樂會(huì)。”
中音在線:在線音樂學(xué)習(xí)門戶
相關(guān)內(nèi)容
- 上海音樂學(xué)院教授陳應(yīng)時(shí)逝世,他讓敦煌古樂奏出新聲2020-6-15
- 新疆民族樂器制作傳承人 制作的民族樂器深受顧客喜愛2020-6-15
- 讓藝術(shù)教育成為生命教育的有效載體2020-6-15
- 梅花獎(jiǎng)演員曾靜萍:讓梨園戲成為藝術(shù)時(shí)尚2020-6-12
- 藏在民居里的手工吉他工作室 李洋從樂手變琴師2020-6-12
- 蘭州民歌傳承人周愛忠:民歌是扎根在泥土上的藝術(shù)之花2020-6-12
熱點(diǎn)文章
熱門標(biāo)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