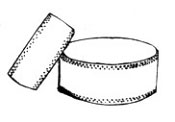中國指揮家余隆登上國際權威的古典音樂雜志《留聲機》封面
中國指揮家余隆登上國際權威的古典音樂雜志《留聲機》封面
中國指揮家余隆登上國際權威的古典音樂雜志《留聲機》4月刊封面,余隆成為首位登上這一權威古典音樂雜志的中國指揮家。該期雜志以《望穿東方》為題,刊發了古典音樂在中國的專題調查。

《留聲機》雜志封面
《留聲機》報道了余隆率上海交響樂團與世界著名古典音樂廠牌柏林德意志留聲機公司(DG)的唱片合約,以及上海樂隊學院、廣州交響樂團、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的發展現狀,并對余隆、馬友友等音樂家進行訪問,描繪中國交響樂的發展版圖。

余隆指揮DG120周年太廟音樂會
《留聲機》報道稱,“余隆的影響力滲透到中國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完美契合特勞特曼言及的‘文化企業家’,以及‘中國卡拉揚’的稱呼。”余隆作為北京國際音樂節創始人,上海交響樂團、中國愛樂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的總監,“太容易讓人想起老一輩國民指揮”。《留聲機》還表示,“也許在從今往后的一個世紀內,世界的舞臺上將不僅能一直聽到中國培養的音樂家,還有中國的音樂創作。”

從1992年發起北京新年音樂會,到1998年創辦北京國際音樂節,再到2000年一手組建中國愛樂樂團,創辦上海夏季音樂節、上海艾薩克·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上海樂隊學院、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余隆領行業風氣之先,為中國古典音樂事業朝著國際化、專業化道路發展不遺余力。而且,他積極推動將有分量的中國作品帶到世界的舞臺上,讓世界通過中國作品更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的人文理念。可以說,在余隆先生的大力倡導下,當代中國最杰出的一批作曲家作品在國際舞臺上獲得空前的影響力。

第二十一屆北京國際音樂節閉幕式音樂會,余隆攜手馬友友、吳蠻演繹BMF聯合委約的《逍遙游》
創刊于1923年的《留聲機》雜志,是當今世界最具權威性的古典音樂刊物之一。該雜志以全球著名唱片品牌的最新發行、錄音史上最經典錄音、國際古典樂壇新聞、最偉大的音樂家及音樂歷史事件等作為著眼點,對國際古典樂壇進行全方位報道。《留聲機》雜志見證并推動了世界唱片工業發展的整個進程,每年一度的“留聲機大獎”更是全世界古典樂壇的盛事,成為與“奧斯卡”、“格萊美”比肩而立的行業重要評獎。
余隆是活躍于國際樂壇的最杰出的中國指揮家,被紐約時報譽為“中國古典音樂屆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現任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委員會主席和中國愛樂樂團藝術總監,上海交響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上海夏季音樂節的聯合總監,以及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客席指揮。
余隆與世界各地眾多知名交響樂團和歌劇院有著廣泛合作,他指揮過的樂團有紐約愛樂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費城交響樂團、洛杉磯愛樂樂團、蒙特利爾交響樂團、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辛辛那提交響樂團、巴黎管弦樂團、班貝格交響樂團、漢堡國家歌劇院、柏林廣播交響樂團、萊比錫廣播交響樂團、漢堡北德廣播交響樂團、慕尼黑愛樂樂團、悉尼交響樂團、墨爾本交響樂團、BBC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團、東京愛樂樂團和新加坡交響樂團等。2008年,余隆指揮中國愛樂樂團作為首支中國樂團在梵蒂岡城保羅六世禮堂為教宗本篤十六世演出,成為令全世界矚目的重要文化盛事。2018年,余隆簽約德意志留聲機公司并在全球發行唱片。
余隆的藝術生涯涵蓋指揮和藝術管理領域。1992年,余隆擔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同年,他參與創辦了中國的新年音樂會系列,并連續三年擔任指揮。1993年起,余隆連續五年為香港市政局指揮歌劇演出。1998年,余隆發起創辦了北京國際音樂節,并連續二十年擔任藝術總監。在他的出色領導下,北京國際音樂節已躋身于全球最重要的音樂節之列。同時,他于2005年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創辦CISMA廣州國際音樂夏令營并連續三年擔任主席,并于2010年先后創辦了MISA上海夏季音樂節和廣東亞洲音樂節。
余隆1964年出生于上海的音樂世家,自幼隨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學習音樂。后求學于上海音樂學院和德國柏林高等藝術大學。鑒于余隆在推動當今世界古典音樂事業發展和促進國際間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突出貢獻,2002年,德國萬寶龍文化基金會向余隆頒發了年度“萬寶龍卓越藝術成就獎”;2003年,法國政府特別授予余隆“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意大利政府向余隆頒發了“共和國騎士勛章”;2014年,他獲得象征著法國最高榮譽典屬體系的榮譽軍團騎士勛章。2015年,余隆榮獲由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頒發的“全球公民”獎,以及由耶魯大學音樂學院頒發的“桑福德獎章”。2016年,余隆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外籍榮譽院士。并于同年被授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十字勛章。
在中國,余隆于2010年被授予“年度中國文化人物”稱號,并于2013年獲頒國家級學術機構主辦的最高藝術大獎“中華藝文獎”,同年,中央音樂學院向余隆頒發榮譽院士證書,以表彰他對中國音樂的發展和對外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貢獻。2015年,余隆獲頒“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現余隆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職務,也是第十一、十二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附:《留聲機》雜志全文翻譯
《望穿東方》
人們一直說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西方望穿東方會給全球音樂版圖及我們所聽的音樂帶來何種影響?如下是安德魯·梅洛的調查。
只要在上海的法租界閑庭漫步,便能看到一塊典雅的木板上畫著一個老式的點亮的電燈泡。這是上海交響樂團的廣告專案,告訴著這座擁有全球第二大人口都市的居民,電燈首次在這座城市啟用是1879年,那也是上海交響樂團成立的年份。廣告語“自1879年點亮城市”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樂團的140周年慶上。這句標語很簡潔,但與一月某個周日夜晚與我一同出席音樂會的聽眾相干甚少,因為他們對科技的興趣可能并沒有那么年代久遠。倒是我身邊的零零后如饑似渴地聽著張昊辰彈的拉赫瑪尼諾夫,然后把照片分享到朋友圈。
要說上海交響樂團的歷史比英美大部分樂團都悠久,可能讓人難以置信。我們常說中國是古典音樂的新軍,代表著未來而不是過去。但我們其實有必要重新認識這個國度,尤其是在當下她與西方的關系正面臨的陣痛興許會形成重大影響的情況下。當整個世界的經濟學家都等著唱衰中國時,中國特色的馬克思資本主義帶來了讓干部們自己都未曾預料到的增長。而當音樂界才剛剛不再把中國音樂家的現象級崛起歸功于讓人瞠目結舌的炫技(也就是對模仿前輩大師比培育包括豐厚而獨特的樂隊文化在內的所謂傳統更感興趣),中國又一次讓我們自亂陣腳。DG去年十月份開啟120周年慶是在北京而不是柏林,主角是全新簽約的上海交響樂團。
即便不是經濟學家,也不難發現DG與上交的簽約關乎中國市場的規模。“文革”結束后,對解禁的西方古典音樂的興趣與日俱增。意志堅定的中產階級視音樂教育為重中之重,如今演奏鋼琴的琴童多達4000多萬。對于唱片公司來說,只要把唱片當做學習輔助工具,或者在家里隨意響起幾首莫扎特或貝多芬的奏鳴曲,這些都足以構成可觀市場。在線播放的發展有效緩解了這一地區長久以來令人頭疼的實體唱片盜版問題。“中國目前是全球錄音產業的十大市場之一,而且是經過授權的錄音,”DG總裁克萊門斯·特勞特曼博士在柏林與我通話時說道:“年輕人的興趣加之移動技術的普及都意味著有增長空間。”這是實打實的增長,據信中國會馬上會從十大市場躍升到五大市場之一,也許是前三大。
那憑借為西方樂團灌錄唱片,品牌被國人奉若至寶,DG就可輕取這個市場了嗎?DG的策略顯然兼顧了戰術和藝術。特勞特曼解釋了簽約一支亞洲頂尖交響樂團的文化寓意,回顧了數年前在琉森音樂節聽到的“具有難以置信高水準”的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出。除此之外,總有樂團以外的弦外之音:“卡拉揚和伯恩斯坦不僅僅是音樂總監,他們也是文化企業家。”特勞特曼提到DG上個世紀的這兩位當家紅人:“在與上海交響樂團及其總監余隆的合作中,我們找到了近似的特質。余隆是一位不管是給中國本土還是國際社會都帶來巨大文化變革的指揮家。”
上海交響樂團的歷史是外來文化在上海的變遷史。樂團早期上世紀初有相當一部分俄羅斯及猶太音樂家,隨后吸收了直到1943年還控制著徐匯區的法國人的文化。2014年,樂團駐扎進由磯崎新擔任建筑設計,豐田泰久擔任建聲設計的時髦音樂廳。音樂會開始前數小時票販子就在街上排起了隊。上交并非上海唯一的樂團,上交當下樂季也不僅僅演出西方的古典音樂。圣誕節前,喬治·本杰明的《切膚之痛》音樂會版連演兩場。
“這是一座大都會,我們樂團的運作也與其多樣性相呼應,”王曉霆是上交的節目總監,他操著一口婉轉地道的英語,回顧著最近演出的布里頓《戰爭安魂曲》、理查·施特勞斯《艾萊克特拉》以及史蒂夫·萊奇的系列音樂會在開票后數分鐘內便售罄。“我在西方幾座城市生活過,熱愛他們的文明。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西方變得止步不前,優秀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因為社會停滯了。在這里,遍地都是機會。”
上交的聲音和創意一樣旗幟鮮明。周日音樂會首先是演奏靈活的拉赫瑪尼諾夫第一鋼琴協奏曲,隨后由指揮李心草執棒的西貝柳斯第二交響曲扣人心弦,比我在赫爾辛基聽到的大部分西貝柳斯都更言之有物。在李心草棒下,音樂結構明晰,節奏動力一路推進把握到位,在不拘言笑中精巧地談笑風生又不失色彩(包括韻味十足的銅管)。
上海交響樂團在中國與日俱增的樂團版圖中名列前茅。一批新興城市的迅速崛起加之不甘落后的攀比下,中國現如今約有80支類似的樂團。不少樂團都在一邊掙扎著物色演奏員,一邊尋求生存空間。“中國樂團缺的是兩樣東西:其一是人員配備,其二是保證高演奏水準的體系,” 上海樂隊學院(SOA)執行長何大耿說。上海樂隊學院由上交成立,旨在提升樂隊演奏文化,這點在剛剛起步,正越來越從這個國家的過去吸取經驗教訓的樂團建設中行之有效。
正當DG去年秋天慶祝第120個年頭之時,中國也在紀念“改革開放”4周年。上世紀七十年代,市場經濟興起,政府鼓勵人們借鑒歐美市場的成功經驗,試圖讓中國變得更加自給自足,從相對自治的樂團身上還是能看到中國經濟的縮影:以夷制夷。何大耿說:“我們研究了歐美樂團人員現狀。歐洲樂團有很多見習機會,但少有國家層面的樂隊教育。美國有類似于新世界交響樂團的半職業化樂隊,但因為工會關系很少有見習機會。曼哈頓音樂學院有著成功的樂隊演奏課程,但局限于學院的資源。在上海樂隊學院,畢業就能獲得碩士學位,每年和上交演出1-12場是必修課。”作為合作伙伴,紐約愛樂樂團提供師資。
上海樂隊學院現有17名畢業生,他們在上交及世界各地的樂團任職。基于“摸著石頭過河”的發展理念,兩位數的中國樂團正在迅速成長不在話下,其影響力則走出國門。我們總是以為亞洲的樂團是靠西方演奏員提味,但事實恰恰相反。我所聽的那場音樂會,來自歐美的樂隊演奏員只有四五位,就人才輸入而言,很多情況下都是單向的。舊金山、倫敦和慕尼黑的樂團從北京、首爾和臺北招募樂師,反之不然。
偶像明星如郎朗對基層器樂教育依舊影響甚巨。有人覺得中國功成名就的音樂家都是單干戶,何大耿對此一邊樂見其成,一邊解釋應對之道:“經常有演奏員考進上交,他們的考試成績非常優秀,但只在樂團里工作了幾個月就離職了,因為樂團的紀律和獨奏家的生活截然不同。我們認為必須要補上這兩者之間的缺口。”
他所說的“我們”肯定包含指揮家余隆。余隆的影響力滲透到中國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完美契合特勞特曼言及的“文化企業家”,以及“中國卡拉揚”的稱呼。作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始人,上海交響樂團、中國愛樂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的總監,余隆太容易讓人想起老一輩國民指揮。
這位留學歐洲的中國音樂家素以改變中國音樂版圖聞名。“大部分人都有所保留,但余隆想什么說什么,人們聽得進去,” 我問馬友友余隆為何卓有成效,馬友友回答道:“他很清楚中國需要什么,他便給到什么。這是他的工作方式。”
在中國南部,環境相對寬松的珠江三角洲國際港口都會廣州,人們可以看到余隆對中國日漸成熟的樂團建設的另一番影響。“隨便問,我希望我們像朋友那樣對話,”這位指揮家在廣州交響樂團五層樓的辦公大樓里與我會面。16年前,余隆出任廣州交響樂團總監,如今樂團在他的帶領下成為中國樂團的佼佼者。雖然與余隆聊了很多,但恰恰是與余隆部下史振江閑坐在樓下草坪上的時光,我才對這里正在發生的一切有所了解。目前,廣州交響樂團的青少年交響樂團正在為本地區迅猛發展的其他青年樂團培養200名指揮,培訓科目都不是在音樂學院學得到的:排練規劃、出版和版權、聲部配置。言下之意就是廣東省至少有著200支青年樂團,而廣東省人口只占中國內地總人口8%。“并不說他們都是完整編制的交響樂團,但畢竟都是樂團,” 史振江說道。這個國家音樂各個方面的增長都讓人瞠目結舌。
規模是一方面,人才是另一方面。我在廣州逗留期間恰逢第三屆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YMCG),這是由余隆發起并由共產黨全力支持的年度學院,看似冠冕堂皇的標題之下其實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培訓機制。由馬友友組建的老師團隊來自絲綢之路合奏團及全球各地的樂隊,他們輔導年輕音樂家,最后則以一臺音樂會收尾,但培訓同樣重視即興演奏、合作創作和非音樂方面的交流。大部分學員來自中國,少數來自國外。一位瑞士科學研究員演奏小提琴,一位日本小號手正在攻讀工商管理碩士。
為期11天的音樂周,馬友友親力親為,甚至于坐在音樂周樂隊大提琴聲部后面拉琴,他說:“我們在這里傳授不少東西,但最主要的是發問:二十一世紀的音樂家需要什么?音樂對于文化、社會和人類起到什么作用?”他鼓舞人心的公開發言《內容、交流與接納》大受歡迎。
音樂周一開始,我就進駐學員隨機搭配的三個小組,看他們花了幾天時間準備一首基于中國民歌的沒有記譜的曲子。每個小組從最初的遲疑不決到后來興高采烈的演出都發人深省。周六晚的音樂會,他們各自演出自己準備的曲子之后是更多的西貝柳斯:由邁克爾·斯特恩指揮的第五交響曲,信心百倍的演出解答了很多音樂結構捉摸不定的疑問。
音樂周旨在為卓有成就的中國音樂家打開國際視野。在更大的層面,甚至可以說是說服中國音樂家找到并培育出屬于自己的聲音。“我們種下種子,未來會收獲到思想、概念和關系,”余隆說道:“青出于藍勝于藍。”當我們聊到中國和西方世界漸行漸遠時,余隆打了一個比方:“人們要學會互相聆聽,就像演奏室內樂。中國是個泱泱大國,有時北方的人聽不懂南方的話。然后是中國之外的世界。但當下我們有那么多年輕人愿意學音樂這門世界性的語言,這樣他們可以互相交流。”
馬友友的亮相似乎是在默默述說中國需要為重紀律輕表達(更何況繼承自蘇聯體系森嚴的師生關系)的音樂教育松綁。“這是另一種學習,一種全新的接觸音樂的方式”,年輕的中提琴學員告訴我:“即興演奏有助于你放下來,被要求展示自己時很過癮。這里的環境鼓勵我們這樣做。”許多音樂周的老師都說看到能力出眾的學員意識到技術是為表達服務的,而不是反過來。“要學習音樂,就要思考自己為什么要演奏,”擔任弦樂組教員的布魯克林騎士四重奏大提琴家邁克爾·尼克拉斯在下課時說道:“這是我們在這里強調的。”
音樂周閉幕音樂會上有位稀客。這位叫亞歷山大·布羅斯的美國人從東北部城市天津遠道而來,他在天津正在籌備建立天津朱莉亞音樂學校。基于西方機構在東方尚存美名,這家位于紐約的知名學府堅定不移地要把這一美名兌成美金。
對于布羅斯而言,這就是生意,他的到訪時如此急迫以致于我縮短了對余隆的采訪。但對西方音樂學院來說,還有比教育行業的商業價值更感興趣的東西。德國的音樂學院免費供亞洲學生就讀,因為他們能豐富學習環境,為當地音樂生活輸入新鮮血液。《留聲機》撰稿人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RAM)校長喬納森·弗里曼-阿特伍德表示同意:“中國學生到精致的歐洲城市,能夠迅速吸收全新的風格和時尚,并能快速展現個性,這令我的同事和我都印象深刻。只要打開一扇窗,他們就能飛過去。”
過去15年來皇家音樂學院的中國留學生數量穩步增長,但要到倫敦就讀不是一件易事,學生必須獲得教員或大師班授課者的推薦才行。不過學生們來到西方就是為了擇善而取的教育機會,這也是上海樂隊學院或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力圖在中國填補的空缺,只是都還不成規模。直到它們遍地開花之前,皇家音樂學院和其他類似的音樂學院都會從中國獲益。
那些想要知道中國其他樂團要過多久才能達到上海交響樂團細致入微演奏水平的人,或許可以從這些教育層面的全新嘗試中找到答案——至少弗里曼-阿特伍德對此很感興趣。“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音樂家其實離更高境界的表達只差一口氣,” 他形容一些他所聽過的中國樂團:“不管他們有多優秀,總有一些還沒有捕捉到的。當然,聆聽一支樂團能夠出色演奏用另一種文化表述的音樂,總是振奮人心的。”既然談及,那么思想交流知否也可以逆轉呢?“是的。我期盼著英國有一天能夠英雄不提當年勇,從中國身上看到他們在短時間內取得的巨大成就,然后反過來自問‘我們能學到些什么?’”
我們能學到很多。上海樂隊學院和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的某些課程即使在西方也很少見(即興,自由演奏,與民族音樂的對話),而且我們的社會已經更多把音樂視作可供剝削的商品而不是可貴的藝術原則。毋庸置疑其中有些部分值得我們長期學習,但我們很快就能耳聞來自中國的聲音,感受中國的尊嚴。上海交響樂團首張為DG在錄音室錄制的唱片將于今年晚些時候發行,夏天樂團將在一系列頂尖的歐美音樂節亮相。唱片收錄的曲目和巡演有許些近似,反映出中國與鄰國俄羅斯一衣帶水的歷史淵源(拉赫瑪尼諾夫《交響舞曲》),還有繁榮的全新創作的樂隊作品,在這里則是陳其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新作《悲喜同源》,由馬克西姆·文格洛夫獨奏。
圍繞中國音樂及中國樂團的話題會因為是拿來主義還是占為己有而變得極為復雜。特勞特曼提到“知名的中國或在中國出生的作曲家是音樂廳里上演的常客,也都由大型的出版公司代理”,其中最負盛名的一批都生活在西方,接受西方的創作委約和演出邀約。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對音樂的想象力源自西方樂團及他們常演的作曲家。
如果過去二十載試圖在證明些什么,那就是在中國。隨著這個國家的樂團百舸爭流,中國對西方日漸產生的敵意會否催生出對本土聲音更深層次的挖掘?汗牛充棟的人才會確保這一挖掘碩果累累。遙想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早期,伴隨著歐洲偉大音樂杰作的是思想開明的民族主義,以及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歷史未嘗不可重復。也許在從今往后的一個世紀內,世界的舞臺上將不僅能一直聽到中國培養的音樂家,還有中國的音樂創作。
中音在線:在線音樂學習門戶
相關內容
- 紅歌唱遍全國的著名音樂家王玉西2019-4-2
- 歌唱家廖昌永:用音樂把詩歌傳唱開來2019-4-2
- 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劉月寧:用中國音樂講好中國故事2019-3-29
- 鄭小瑛:音樂是人民創造的,需要把音樂普及給觀眾2019-3-26
- 山東藝術學院副院長:加強文化藝術人才隊伍建設2019-3-25
- 湖北科技學院音樂學院王群益:讓音樂陪伴山村留守兒童成長2019-3-22
熱點文章
熱門標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