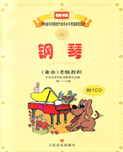試論作曲家在即興音樂創作中的心理動向(二)
導語: 摘要:即興音樂創作作為一種相對于文本音樂創作更為靈活和自由的音樂創作形式而獨立存在。在這種特殊的創作形式中,作曲家沒有足夠的時間按照文本創作的動機發展模式邏輯地、理性地并高度依賴傳統作曲技法來寫作,而是一種感性占據主要地位的創作模式。然而,無論這種一維性的創作中“感性”與“偶然”占據何等重要的位置,作曲家的創作與演奏習慣仍作為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與這些“感性”和“偶然”一同貫穿于整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 關鍵詞:即興創作 音子 習慣 鏈式發展 在詳細論述文章主體思想之前,有兩個音樂學專有名詞需要作出詳細解釋。一個是“即興創作”,另一個是“音子”。 即興創作是相對于“文本創作”而命名的一個音樂學名詞。但在事實上,往往不同的音樂家對即興創作這一概念的默認范籌不盡相同。早在二十世紀末的一段時期內,部分音樂美學家就已提出應賦于“即興創作”這一名詞更明晰的解釋。他們認為應將“即興創作”分為廣義與狹義兩個概念,并指出各自的含義,即:狹義的即興創作是指作曲家完全脫離筆下創作形式而介以某種樂器為媒體所即時演奏的音樂作品。廣義的即興
這一反應原理還可這樣去解釋,即如果筆下創作的動機式發展或者說是樂思的展開是模式化占主導地位的一種創造,而我們則應當把這種將音子演進作為一種相對更具張力的實踐。而這時的音子雖不是“純理性”、“純邏輯”地展開,卻也隨著它的演進而逐漸具備了一定的動機意念,音子的意義也就從起初的偶然出現,逐漸上升為音樂發展的原始細胞。因為我們知道,一旦音子偶然出現,無論是演奏者還是聽眾都會往往在潛意識中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這幾個音上。在這種情形下,嚴格地說這種現象自身就存在著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作曲家在這種創作性的演奏中有意地盡量避免無理性素材的出現,而另一方面卻又必須將這些已經出現的偶然材料作出相應的合理詮釋,并圍繞它們添枝加葉,使之在聽覺上趨于順暢。有過即興創作經歷的人幾乎都會有同樣一種感受,那就是當音子出現的一瞬間心里便不自覺地把精力放在它們之上,并且在起初的那一瞬間的感覺并不是要將它們發展成為動機式的結構,而僅僅只是一種順應心理,有時甚至感覺是一種無形的心理負擔。畢竟這些偶然的音響片段要給耳朵與心靈一個交待和相對合理的表述。但這種心理處境的發展總是要比起初想象的好,因為音子往往在發展開來后會將聽者及演奏者本人一并帶入一個意想不到的境地,當事人起初的迎合心理漸漸隨著音樂的發展而漸漸趨于平靜,有時甚至是意想不到的驚喜。也許正是這個原因,肖邦才在那次鋼琴作品音樂會上大驚失色地自語說:“怎么可能?我居然在幾分鐘內創作了我多年來最想要的,也是最另我意想不到的音樂作品。”
然而,我們在認識到即興創作的偶然因素地位的同時,并不能否認作曲家創作習慣的作用。這兩種原理其實是一種“矛盾與統一”的關系,我們只強調任何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不附合作曲家在即興創作中的真實心理反映,我們理當從正反兩面來論證。
事實上,無論我們如何強調即興創作中感性作用和偶然因素的地位,都必須認清這種感性作用與偶然因素始終是在作曲家的“創作習慣”與“演奏習慣”中進行和發展的。上升到哲學角度上說,這即是部分與整體的邏輯關系,又是矛盾與統一的全部過程。這一點不難理解,我們可以從一個很小事例來說明:從肖邦的即興音樂作品中我們找不到巴赫的作品風格,正如在約翰·凱奇的即興鋼琴作品中找不到李斯特的作品風格一樣。另外,如果要認識那些偶然因素與創作理性的關系,我們可以去聆聽幾遍趙曉生在07年5月所創作的即興鋼琴新作--《西夏印象》,這是一部描寫八百年前廣袤的西北大漠中一個有著一百八十年輝煌歷史王國的作品。此作品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結構更自由,創作手法更隨心所欲,某些音的出現在一瞬間給人的印象是“闖”進來的,然而很快它就成了展開的對象,甚至這種現象會在這部作品中連續出現多次,但無論這些突如其來的“音”來臨時讓人感到如何措手不及,它們最終總在那種震天動地、信馬由韁的音響世界中越來越趨于合理,越來越顯得必要,但最終它們并沒有脫離趙老的作品風格,反而成為他即興創作中的有利工具。
事實的確如此,作曲家在長期的音樂創作過程中所形成的個人習慣與風格必然在無形中左右著他們的創作思維,即便是感性占據主要地位的即興創作也不例外。正如韓鐘恩先生所述:“作家與作曲家是置‘感性’與‘理性’當中,并且表達一種合適。但是,兩者雖然矛盾卻常常攜手在一起。”因此,我們必須在強調“文本”與“即興”、“感性”與“理性”的同時更不能否認它們之間的統一性原理。換句話說,“偶然”在即興音樂創作中有重要作用,但卻不是整個創作過程的惟一抽象來源,甚至不少音樂家將“即興創作”這一概念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存在的“疾速筆下創作”。當然,這一觀點錯誤地否認了這種一維性創作的隨機性,明顯是一種片面的說法,但若單單從音樂的“邏輯展開”而論,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在看待這一問題時必須客觀全面地、辯證地來對待和分析,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認知這種看法的態度時并不應該簡單地加以“褒揚”和“抵抑”,而是以相對的,多層面的心態和觀點來對待。
今天,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價值觀念與文化觀念高度多元化的時代里,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作曲家對即興創作這一現象不再單純地持以褒貶,并欣然走上即興創作的道路。屆時,即興創作必將作為一種獨特的抽象載體去承載更多作曲家心海深處的潛在心聲,并最終將他們的本意與初衷解讀給越來越多的聽眾。
參考文獻
[1] 越曉生《中國鋼琴家專輯——后記》(河南電子出版社)1990年版
[2] 韓鐘恩《音樂試圖將音樂作為音樂來擺脫》(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3] 韓鐘恩《詩人與作家》(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4] 于潤洋《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長沙,第1版
[5] 姚恒璐《二十世紀作曲技法與分析》(上海音樂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相關內容
- 如何避免練習鋼琴時的不良習慣 2014-11-24
- 如何防止過度練習產生的傷害 2014-11-18
- 提琴 | 面對攝像機你該怎么拉?2014-11-18
- 中央音樂學院琵琶考級演奏文憑級教材目錄2014-11-17
- 中央音樂學院琵琶考級9級教材目錄2014-11-17
- 中央音樂學院琵琶考級8級教材目錄2014-11-17
熱點文章
樂器
鋼琴的發展史
鋼琴(piano forte或forte piano),簡稱piano,是一種鍵盤樂器,用鍵拉...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