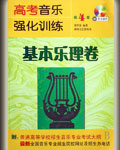著名音樂理論家、教育家,百歲學人繆天瑞(一)
導語: 望九之年的學者不多,望九之年還在寫作的學者更不多,百歲高壽仍然筆耕不輟的學者就如鳳毛麟角。而像繆天瑞這樣已達百歲高壽還在跨入21世紀后的幾年間寫出十余萬字的學者,恐怕真是獨步海內、絕有無雙了吧!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著名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繆天瑞先生,1908年4月15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鎮,他是第三、四、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人民音樂》主編、天津音樂學院院長、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長兼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長,是改革開放后國務院批準的第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1999年榮獲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特別獎”。 1983年,已過古稀之年的繆天瑞先生,婉辭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音樂學院院長一職給予的優厚待遇,甘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當一名普通的研究員,靜靜地研究那伴隨著“效鳳凰之鳴而造律”的神話一起誕生的古老的樂律學。如同“中國古代音樂史”永遠與楊蔭瀏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樣,“律學”也永遠與繆天瑞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他們奠基性的研究成果,讓一個個具有古老傳統卻
望九之年的學者不多,望九之年還在寫作的學者更不多,百歲高壽仍然筆耕不輟的學者就如鳳毛麟角。而像繆天瑞這樣已達百歲高壽還在跨入21世紀后的幾年間寫出十余萬字的學者,恐怕真是獨步海內、絕有無雙了吧!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著名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繆天瑞先生,1908年4月15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鎮,他是第三、四、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人民音樂》主編、天津音樂學院院長、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長兼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長,是改革開放后國務院批準的第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1999年榮獲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特別獎”。
1983年,已過古稀之年的繆天瑞先生,婉辭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天津音樂學院院長一職給予的優厚待遇,甘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當一名普通的研究員,靜靜地研究那伴隨著“效鳳凰之鳴而造律”的神話一起誕生的古老的樂律學。如同“中國古代音樂史”永遠與楊蔭瀏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樣,“律學”也永遠與繆天瑞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他們奠基性的研究成果,讓一個個具有古老傳統卻未按現代學術理念重新梳理的研究領域,在20世紀學開新境,化迷途為通途,變絕學為顯學,也使這一個個研究領域永遠與他們的名字聯系在一起,而人們也將永遠把他們的名字與中國近現代史上創立了新興學科的先賢們相提并論。
繆先生在學術領域的代表作《律學》歷經三次修訂,從成書到最后一次修訂,整整跨越了半個世紀,他為《律學》最后一次寫序時,已是八十有五了。一部學術著作歷經如此大幅度的增修,也是學術史上少有的學案,作者那種決不固步自封、不斷超越的進取精神、執著精神可見一斑。因為他的《律學》,中國音樂學界創立了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與自然科學聯系最密切的學科,并建立了一個因為首屆會長的品格而學風崇實的學會。樂律學是音樂學中技術最繁難的領域,它強烈的民族特性和數理規律相互摻涉,向來乏闡義理。繆先生的敘述深入淺出,尤其后期著述中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超脫,對世界各民族“音體系”的平等敘述,使那種因為數理規律掩蓋了民族性的學術理念彰顯出來。
繆先生對中國音樂界的最大貢獻還有由他主持的《中國音樂詞典》(正編、續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音樂百科詞典》等辭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這一系列卷帙浩大的詞典,成為我國音樂界第一批權威的工具書。一個領域的工具書決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詞典,編輯一個學科的辭書,就是要把代表著國家學術水平的知識體系梳理成序,歸置列張,小至一個術語的規范隸定,大至一個概念的歸納界說,宏綱細目,按部就班,這就是學術界之所以看重一個學科辭書的意義,也是這項工作的價值所在。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一個學科、一個研究領域是否成熟的標志性成果之一。20世紀初,楊蔭瀏先生曾經感慨:什么時候可以有一本查找中國音樂知識的詞典啊!楊先生帶領中國的音樂學家們對傳統音樂的大部分品種進行了普查,為中國音樂的知識體系提供了基礎性框架,但他沒有來得及完成這項歷史使命。完成這項由楊蔭瀏先生表達出的所有中國音樂家夙愿的使命,就落在繆天瑞先生為代表的一大批心同此愿、志同道合的戰友們身上了。繆先生以超常的勤奮埋首于這項煩瑣繁雜、千頭萬緒的工作中,由于事必躬親的主編具有的崇高威望,由近百位學者參與撰寫條目的詞典終于沒有辜負中國音樂界半個世紀的期盼,《中國音樂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于楊蔭瀏先生離世的1984年面世了。出版后,被兒女們稱為“辭典迷”的繆先生似乎意猶未盡,如醉如癡,又一口氣獨自編輯了融會中西、數百萬字的《音樂百科詞典》。
相關內容
- 福建師大音樂學院編撰完整古代音樂文獻2014-12-2
- 沒有老師,20萬的音樂器材閑置2014-12-2
- 讓孩子笑著合唱2014-11-19
- 民族歌劇不是擴音的借口2014-11-19
- 做音樂的智者2014-10-29
- 文宣創意也要拼膽略2014-10-29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