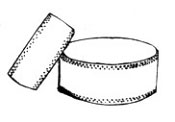疫情下的身障藝術家——演出基本停滯卻從未放棄創作
疫情下的身障藝術家——演出基本停滯卻從未放棄創作
演出基本停滯,殘疾人藝術團虧損將達700萬元,藝術家適應新的生活不便,業內轉型自救互幫互助
疫情下的身障藝術家,從未放棄創作
疫情期間演出行業基本停滯,這讓本身生活不便利,平時主要依靠現場演出收入的身障藝術家們舉步維艱,殘疾人藝術團今年虧損預計將達700萬元。但藝術是他們與世界的溝通,演出是最重要的載體,他們的需求不能被忽略。
幾位視障音樂人、身障藝術家和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藝術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他們由于演出取消,基本已經沒有穩定收入,同時還面臨著疫情期間更多生活上的不便,但他們正在積極找尋新的轉型方式,目前也有民營演出機構在力所能及地對他們進行一些幫助,只是在普通藝術家紛紛轉型、跨界或者積極推動線上演出的同時,身障藝術家卻尚未獲得更多的援助,似乎還沒有探索出更多自救的方式。
生活現狀
學會點外賣,殘疾人藝術團靠積蓄運轉
視障音樂人周云蓬生活在大理,這段時間一直為自己的新專輯錄音。原本每年3月都是開始巡演的日子,樂隊巡演加上商業演出,差不多會有五六十場,能把全國走一遍。現在周云蓬只參加了“相信未來”和“長不大的童謠線上音樂會”等幾場公益線上演出,原計劃年中的盲童夏令營,帶著孩子們去觸摸沙漠和黃河也被擱置了。他在微博說:“難啊!不過全人類都如此,想一想,也就不想那么多了。”
這段時間的出行限制讓周云蓬學會了用手機在網上下單買東西叫外賣,依然保持每天五六個小時閱讀的習慣和上網了解資訊。他在微博里關心世界,表達自己的感想。有一條微博說到聽朋友說大理的天空特別美,美到無法用語言形容,他自己也很高興,“替別人高興,為不屬于自己的幸福祝福”。他憧憬著,等疫情結束,能帶著導盲犬熊熊去周游世界,有時候發微博,他還會特意更正一個錯別字。他開玩笑說,這個世界是跟你有關系的,不上網的話,萬一哪天可以演出了,可能就只有你還不知道呢。
魏菁陽是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聾人舞蹈演員,以往平時每個月都有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動,多則整個月,少則幾天。她記得去年年底的藝術團總結大會上,團領導在部署2020年工作計劃的時候特意強調了今年的國內外演出任務很多、很重,可是突發的疫情讓已定的上半年演出全部取消。
同為殘疾人藝術團聾人舞蹈演員的陳靜去年演出了156場,平均三天演出一場。今年1月時演出檔期被安排得爆滿,演員被分成兩撥,分別參加泰國“歡樂春節行”和央視春晚的演出活動。演出結束后大部分演員回老家過寒假,但是剛好遇到了疫情,一些老家在湖北的演員只能繼續留在藝術團生活,團員們在藝術團一待就是四個月,從未出過門,日常學習排練生活都在團里。陳靜最遺憾的就是作為今年即將畢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生,她無法去參加學校的畢業典禮,“來不及報到,就跟學校再見了。”
由于線下演出取消,大多數身障藝術家這段時間都沒有了收入。問到這個問題,大家往往會自嘲又心酸地一笑。殘疾人藝術團團長邰麗華向新京報記者介紹,目前藝術團有工作人員34人,演員包括學員隊97人,今年年初,藝術團就已經確定了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意大利、日本、丹麥、德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巡演,以及國內“共享芬芳·共鑄小康”下基層演出近80場。這些都隨著疫情取消。
藝術團80%的人員經費需要依靠商業演出收入解決,疫情暴發沒有了演出收入,是藝術團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團里目前主要靠以往演出收入積蓄來維持運轉,預計今年將虧損700萬元左右。而藝術團演員們的收入由固定基本工資和演出補貼構成,演出越多收入越多,藝術團能保障基本工資發放已經非常不容易,演員們目前也只能拿到基本工資和少量活動的補貼。
周云蓬跟大多數身障藝術家的狀態一樣——等待演出,節約開銷。他甚至擔心,可能未來可以演出了,但是演出場地已經受疫情重創,難以維持經營后不存在了。但目前除了收入,生活對于他們更是難題。
疫情中,殘疾人藝術團對于團員的出行要求十分嚴格,大多數團員幾乎足不出戶,一日三餐都吃盒飯,每天排練都戴著口罩。由于聽力障礙的人交流是靠手勢語、看口型和面部表情來獲取信息,口罩把面部大部分都遮擋了,也為他們獲取更準確的信息帶來了很多不便。
藝術團的蔣燦是位盲人聲樂、器樂演員,以前的快遞、外賣等收貨上門服務在疫情期間都改成了只能送到小區門口,這也意味著作為一名視障人士的他還要上下樓,取東西比以往要更加困難。原本上下班地鐵出行的他在疫情期間為了做到盡量避免人員聚集,不給更多人添麻煩,不得不改為打車上下班,每個月的工資大部分都要用在交通費用上面。
自救互助
募捐眾籌、轉型線上、做義演
今年5月初,戰馬時代公司收到了曾合作過的葡萄牙盲人音樂家多娜的求助信息。
2017年多娜曾受戰馬時代的邀請來中國北京、武漢、包頭三個城市巡演,她的葡萄牙傳統民謠法朵音樂和視障人士的堅韌生活態度給歌迷和工作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疫情期間,戰馬時代從多娜的歐洲經紀公司了解到,多娜不能上街表演沒有收入來源,也沒有得到任何來自政府的援助,由于需要保持社交距離,隔離期間朋友也很難出門過去援助她,多娜只能封閉在家里,生活狀況非常艱難。
戰馬時代迅速為多娜發起了線上專輯募捐活動,歌迷可以以20元的價格購買迷你數字專輯,其收入全部轉交多娜,讓她能夠在疫情期間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
最終數字專輯賣出去了381張,戰馬時代自己補貼空缺,湊足了1000歐元給多娜。錢不太多,卻是歌迷和朋友們的共同心意。戰馬時代創始人劉釗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消息發布之后反響比預期的要好很多,當天就售出了200多份,有很多行業內的朋友以及沒有看過多娜演出的歌迷也都支持了她,甚至有網友一口氣買了80份,還特別叮嚀工作人員一定要把錢轉交給多娜。
然而這些錢只能幫她渡過眼下的困難,維持基本生活,更長遠的還要看國際疫情控制和恢復工作的進展。戰馬時代創始人劉釗特別強調說,多娜比較幸運的是她還有一個專業的經紀公司可以求助,如果是自力更生的身障藝術家,情況會更艱難。
作為一名演員,蔣燦覺得,比生活上面對難題更困難的是沒有演出的難受心態。
等待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時,殘疾人藝術團也沒有懈怠,積極創編和排練新作品,還為在一線抗疫的醫務工作者創作了歌曲《守護生命》,用他們自己的特殊藝術向醫護人員致敬。殘疾人藝術團的竹笛演奏員譚偉海一直都在抖音進行演奏直播,無臂藝術家黃陽光在快手直播創作書畫。
從1月疫情開始,藝術團就積極轉變工作方式,一方面發揮互聯網的優勢,探索互聯網云演出的新模式,將節目推廣到一些新媒體平臺。比如網絡直播的形式進行“共享芬芳·共鑄小康”演出,還有全國助殘日和六一的在線演出,或者在各個特別的日子里照常錄制節目并播出,另一方面潛心創作,加快推進藝術創新。目前藝術團已經啟動芭蕾舞《我的祖國》、手舞《月光》、特色舞蹈《律動課》等多個節目的創作。音樂方面,抗疫歌曲《守護生命》還獲得了“風雨同歌”——中國抗疫主題MV征集典藏活動金獎。
7月1日晚上,殘疾人藝術團“黨在我心中,共筑中國夢”在線公益義演在中國網播出。藝術團提前一個月就開始投入創作,由于原定攝制組的部分人員隔離和豐臺疫情較重無法參加節目攝制,最終藝術團從兄弟單位借來設備自己拍攝,非專業出身的宣傳部團員們自己提前研究分鏡頭,一遍遍地拍攝,整個拍攝進行了整整四天,演員們就一遍一遍地表演。
和其他音樂人一樣,視障音樂人也選擇了在特殊時期,用音樂鼓舞更多的人。5月初,周云蓬參加了“相信未來”在線義演,演唱《瓦爾登湖》。之后周云蓬和中國盲文圖書館、中國盲人協會、北京市盲人協會一起籌備了一場盲人線上公益音樂會,周云蓬、蕭煌奇和20位盲人音樂人一起演出。
隨后跟環球唱片簽約的臺灣盲人歌手蕭煌奇在騰訊音樂舉辦了“蕭煌奇的周末晚宴”線上演唱會,一連演唱12首歌。他在自己的微博再次表示:音樂是我跟世界溝通的橋梁。
工作之外的關注
1大多數人并不了解他們的生活
2017年葡萄牙盲人音樂家多娜來中國巡演,是戰馬時代的企劃總監Adele第一次跟盲人音樂家合作。領著樂隊成員入住酒店的時候是個傍晚,Adele幫忙把多娜推到她的房間,樂隊成員將多娜的物品放置在熟悉的位置,牽著她的手帶她轉了一圈熟悉空間。臨走前樂隊成員順手把燈關了,Adele下意識的有點詫異,樂手笑了一下說,反正她也用不到,就不浪費電了。這件事給Adele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每想起來都有點好笑又有點心酸。
由于幾場演出都是在劇院,多娜之前沒有上過這個體量的演出,看不見這件事情讓她演出前會比較沒有安全感。通常在第一首歌之后,她會聽觀眾拍手的聲量和反響,如果反響小她會有點緊張,反響好的話就漸入佳境。還好觀眾通常都是越來越熱情的,多娜的表現也越來越好。在簽售環節的時候,多娜簽名是用盲人的點字機打點在紙上的。
隨著接觸更多,Adele發現盲人音樂人的生活非常辛苦,甚至有點無法想象自己如果看不見的話是否也能像她一樣積極樂觀。Adele還記得多娜特別愛吃中國菜,而且要咸香油辣的那種,可能是因為她無法享受其他感官上的刺激,就喜歡吃得更重口一點。多娜喜歡逛公園,在北京期間還去逛了地壇。聽不同環境里的聲音,聽地壇的風聲鳥叫,大爺大媽拉琴唱歌,中國人說話聊天的聲音,對她來說都很新鮮。
崔文嵚則以周云蓬舉例,覺得可能跟一般人的認知不太一樣,殘障人士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實很強,他就很驚訝周云蓬自己還能做飯,操作手機電腦也很熟練。“他的聽覺很靈敏,有一次他在酒吧演出,我坐在很遠很遠的角落里跟朋友小聲說話他都能聽見,還跟我們打招呼。”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助理團長李文倩從大學畢業就來到了藝術團,和團員們一起生活一起成長。與這些殘障藝術家們接觸,她最深刻的體會就是:純真、專注、感恩、陽光向上,永遠對美好生活充滿激情和熱愛。“每當演出結束我站在舞臺的幕側看到他們站在舞臺中央謝幕,接受不同膚色、不同國家的觀眾起立致意,我都非常自豪和驕傲。他們雖然身體上有不便,但是從未放棄夢想,甚至比我們常人做得更好。”
2不尊重的現象仍少量存在
盡管身障藝術家們在生活和演出中獲得的幫助居多,但仍難免會遇到冒犯和不尊重的現象。周云蓬在自己的微博說道:“跟好友們說一聲:見到我的時候,請別說,老周,猜猜我是誰?能聽出來嗎?這讓我心里很別扭。如果你改不了,我再容忍你們18次。但對普通的視障人士,盡量不要這樣詢問。正確的方式是:先介紹自己是誰,然后開始交談。”
周云蓬認為,生活環境需要區分為公共空間和私閉空間,在私閉空間可以不那么脆弱敏感,就像生活中要好的朋友也經常跟他開玩笑一樣,他并不會介意。但是在公共空間里必須要有尊嚴要敏感,如果有人在網上冒犯了這個群體,自己就肯定會發聲。“這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就像很多人不需要走盲道,但是盲道必須存在一樣。尊重是自己的道德底線。”
李文倩則表示過去會有言語和行為上的不尊重,但是隨著社會文明進步,人們已逐漸認識到,身障人士不是不行,只是不便,如果給他們提供平臺,他們一定能創造價值。“藝術團的演員們正是用他們自己的藝術才能,讓全社會更加了解身障人士,尊重身障人士,同時呼吁全社會給予身障人士更多的關心和關愛。同時也告訴所有的身障人士,尊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贏得的。”
3身障人士藝術的發展需要更多崗位
對于創作歌手周云蓬來說,視障音樂人的創作與普通音樂人的差異并不大,大家都面臨著相同的創作困境和優勢,但對于其他身障藝術家,未來依然艱難。
李文倩認為,身障藝術家在表演和創作中最大的不同還是克服自身的障礙。如果跟健全人對比,盲人會因為視覺受限,在舞臺上缺少藝術表現力,缺少與觀眾的互動。聾人聽不見音樂節奏,只能靠熟記動作和節奏加上手語老師的指揮完成演出。聾人用肢體語言表達情感、音樂和節奏,盲人用聲音音樂來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為聾啞人舞蹈家的邰麗華特別關注到了聽力障礙的舞蹈演員們,她認為,身障藝術家很難將藝術作為終身職業,受到生活、身體等條件的限制,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就不得不告別舞臺,尋找新的職業方向。特別是聽力障礙的舞蹈演員,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大多從小就在藝術團學習舞蹈專業,到了一定年齡,傷病、身體條件都無法繼續跳舞,只能退役回到地方工作。由于聽力語言障礙,他們很難取得教師資格證,就不能進入特教學校從事舞蹈教學。舞蹈對于他們只是青春職業,對于未來缺乏職業規劃和出路。
邰麗華特別呼吁說:“我認為針對進入特殊教育學校從事舞蹈教學的聾人,教育部門應該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幫助。他們從小接受舞蹈訓練,同時與聾人之間不存在溝通障礙,更有利于教學實施,應該鼓勵優秀的退役聾人舞蹈演員進入特殊教育學校,帶動各地身障人士藝術的發展。”
記者手記
采訪中,周云蓬老師說了一句讓我很心酸的話——對于很多人來說,演出不是剛需。相比人們生活密不可分的衣食住行,藝術和演出的需求被排在了最后,業內最樂觀的看法是能夠在第四季度逐步恢復線下演出。這也就意味著,這些依靠線下商演、機構幫助組織演出活動維持生活的身障藝術家將在近一年的時間內收入銳減甚至完全沒有收入。
作為身障藝術家,他們需要花費更大的精力來適應生活上的不便,也無法像其他藝術家一樣迅速轉型投入到線上演出中。他們習慣了處于被動的狀態,在全世界各行業都受到疫情影響的時候選擇了默默承受。可藝術是他們與世界的溝通,演出是最重要的載體,即使不能看到這個世界,或者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他們的需求不應該被忽略。應該有更多平臺和機構幫助他們適應與疫情共存的新生活,給予他們更多的展現渠道,找到新的盈利模式。
因為我們也是他們與世界溝通的方式。
中音在線:在線音樂學習門戶
相關內容
- 青年女高音歌唱演員易銘新歌《為你而來》全網上線2020-7-22
- 陽信縣玉友學校音樂老師鞏文化:用音樂和留守兒童一起快樂過暑假2020-7-22
- 對話2020普羅科菲耶夫國際音樂大賽鋼琴組評審曹慧2020-7-22
- 全能曲藝家譚派單弦藝術代表人物趙玉明去世2020-7-21
- 王力宏:學音樂是一輩子的馬拉松2020-7-20
- 關牧村當選為天津市音協主席2020-7-20
熱點文章
熱門標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