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樂家呂遠(yuǎn)的人生傳奇和心路歷程
著名音樂家呂遠(yuǎn)的人生傳奇和心路歷程

呂遠(yuǎn),當(dāng)代著名音樂家,海軍政治部歌舞團(tuán)原藝術(shù)指導(dǎo),曾任中國文聯(lián)委員,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常務(wù)理事、外事委員會顧問等職。在60多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呂遠(yuǎn)創(chuàng)作了1000多首歌曲,近100部歌劇、舞臺劇和影視劇的音樂及器樂曲,其中《克拉瑪依之歌》《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泉水叮咚響》《八月十五月兒明》《西沙,我可愛的家鄉(xiāng)》《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有一個美麗的傳說》等膾炙人口的佳作流傳至今。今天,黨建網(wǎng)微平臺帶您一起來了解這位90高齡老人的人生傳奇和心路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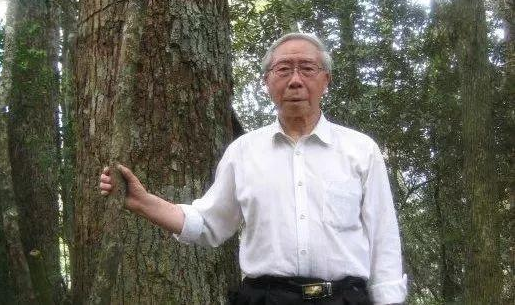
著名音樂家呂遠(yuǎn)
一直以來,經(jīng)常有人問我是怎樣走上音樂道路的,怎樣成為作曲家的,我總覺得不太好回答,不是因為故事精彩情節(jié)曲折,而是因為我一生都是在音樂與文學(xué)、主觀與客觀的矛盾沖突中跌跌撞撞走過來,覺得沒有什么好說的。回顧自己參加革命工作70多年的歷程,就是一個跟著革命隊伍走過來的普通音樂工作者的一生,沒當(dāng)過官,也沒干過什么大事,一直按照黨和社會的需要,想方設(shè)法完成各種宣傳任務(wù)。如果說我有什么成績、有多少流傳的作品,我心里清楚,那些事和作品,本質(zhì)上都是根據(jù)現(xiàn)實生活中人民群眾的需要來完成的,并不完全是我的功勞。如果群眾不認(rèn)可,我一個作品也留不下。我只是在黨的教育培養(yǎng)下,在社會的實踐中,邊干邊學(xué)(包括上大學(xué)),邊改造邊提高,一直走到現(xiàn)在的。
1929年9月,我出生于遼寧安東(現(xiàn)丹東),祖籍山東海陽(現(xiàn)劃歸乳山),讀書是在吉林的臨江。父親是逃荒到東北的農(nóng)民,我出生的時候家里還有點錢,可以供我們兄弟讀書。在我上小學(xué)二年級的時候,父親的一位朋友送給我們弟兄三人每人一把口琴,我喜歡得不得了,每天學(xué)著吹。從四年級起我就胡亂寫詞編歌。13歲我考進(jìn)了礦山學(xué)校(偽滿“臨江國民高等學(xué)校”),在那里開始學(xué)習(xí)西洋音樂,并學(xué)習(xí)曼德琳和小提琴,學(xué)的都是西洋曲子,而且很著迷,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
1945年秋天,八路軍接收了我們學(xué)校。當(dāng)時我并不喜歡他們帶來的革命音樂,感覺那些歌曲很“土”,但沒想到,八路軍戰(zhàn)士和老百姓對我演奏的洋曲子并不報以掌聲,卻很喜歡那些“土”的歌曲。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音樂里的“洋”“土”沖突,于是出現(xiàn)了我白天給《兄妹開荒》伴奏,夜里卻跑到?jīng)]人的地方拉外國小提琴名曲的怪事。后來回想起來,我才意識到那是一段人生迷惘的時期,雖然我有音樂志向和鉆研精神,但還不懂得音樂藝術(shù)對民族和大眾的意義。
真正讓我從“小我”的音樂天地里走出來,還是在參加革命工作以后。1948年我在遼東省(共產(chǎn)黨在解放區(qū)劃的省份)林務(wù)局搞職工文藝工作,除了演奏外還寫些樂曲,群眾的需要迫使我必須選擇民歌小調(diào)的素材,于是“土”成了我的方向,開始逐漸理解音樂的民族性和大眾性。要讓群眾接受我的音樂,我必須演奏他們喜歡的曲調(diào)和形式。在火熱生活中,我找到了情感的歸宿,逐漸認(rèn)識到民族音樂、大眾音樂的情感美和形式美。我慢慢懂得,音樂作為一門藝術(shù),它不是為音樂家而存在的,而是為接受它、喜歡它、欣賞它的人民大眾而存在的。
隨著認(rèn)識的提高,我深感自己的音樂知識太少,理論水平太低,迫切希望能到大學(xué)深造。當(dāng)時解放區(qū)只有華北聯(lián)大和東北大學(xué)。1950年,我請假去長春的東北大學(xué)找到哥哥呂元明,他帶我見吳伯簫老師。吳老師讓我去報考學(xué)校的文工組。等領(lǐng)導(dǎo)批準(zhǔn)我去東北大學(xué)學(xué)習(xí)時,學(xué)校已改名為東北師范大學(xué),設(shè)立了音樂系。于是我就在音樂系完成了系統(tǒng)的音樂基礎(chǔ)理論和文藝學(xué)理論學(xué)習(xí),特別是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理論以及聯(lián)共黨史等課,這對我的世界觀、藝術(shù)觀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那時東北師大的校長是張如心,不久又換成了成仿吾,我很敬佩他們,那么大的學(xué)者,卻那么樸素。我們音樂系的音樂教育也貫徹了延安魯藝的許多理念,系主任李鷹航也是延安來的干部,還聘請延安魯藝的瞿維、莊映,還有不少民間藝人來教課。蹦蹦(二人轉(zhuǎn))、落子(評戲)、京劇、民歌都學(xué),我還在課余去找朝鮮族老人學(xué)朝鮮民歌。從這時開始,我真正樹立了為人民、為大眾、為民族而從事音樂創(chuàng)作的“大志”。
1954年5月,我被分配到在“652工地”(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代號)的中央建筑工程部政治部文工團(tuán)。這個團(tuán)的任務(wù)就是為全國建筑工人演出,我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作品是頌揚(yáng)一個工程連連長模范事跡的大合唱。我還寫過歌唱木工、瓦工、挖土機(jī)手、汽車司機(jī)等各工種的歌曲,都是自己作詞作曲,如《馬車夫之歌》《推土機(jī)手之歌》《木工合唱》《架子工之歌》等等,深受工人喜愛。我的第一首在全國傳唱的歌曲《建設(shè)者之歌》就是那時創(chuàng)作的,這首歌原名叫《建筑工人之歌》(《中國青年》雜志發(fā)表時改成《建設(shè)者之歌》),歌詞是:“從那海濱走到邊疆,我們一生走遍四方,遼闊的祖國萬里山河,都是我們的家鄉(xiāng)……面前總是無盡的原野,身后總是嶄新的樓房,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戰(zhàn)斗著奔向遠(yuǎn)方……”這首歌現(xiàn)在早已不唱了,但我們不能忘了那些辛勤的建設(shè)者。
1956年的中國大地像是花期三月的沃土,原野上人人都在揮汗如雨。幾萬轉(zhuǎn)業(yè)軍人在四面八方尋找石油,包括楊虎城將軍的女兒楊拯陸,也為尋找石油凍死在戈壁灘上。有一天,我在建工部的內(nèi)部小報上看到一則報道:新疆的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地方打出了一眼高產(chǎn)油井。盡管這個題材不屬于我們團(tuán)(應(yīng)屬于石油文工團(tuán)的創(chuàng)作任務(wù)),但我還是決定寫一首贊美克拉瑪依的歌,可是我找不到任何資料,地圖上也找不到這個名字。1958年我被“發(fā)配”到甘肅,我?guī)е啃欣睢①Y料和樂器去了蘭州。我被安排到一個工地上勞動,那兒剛開始建設(shè)煉油廠,去了后才知道就是為煉克拉瑪依的原油建的煉油廠,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在那里邊勞動邊向人們打聽克拉瑪依的情況,還看過一部蘇聯(lián)拍的紀(jì)錄片,叫《阿拉木圖—蘭州》,其中有許多戈壁灘和克拉瑪依的鏡頭,讓我很受啟發(fā)。每天一邊勞動一邊哼哼那些我沒寫成的各種歌曲素材,后來一位木工陳師傅把自行車借給我,讓我每天夜里去他家里寫作,而他住到我那個塵土飛揚(yáng)的工棚里。我白天勞動夜里創(chuàng)作,雖苦猶樂,一個月就完成了《克拉瑪依之歌》和長詩《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手》的創(chuàng)作。我興致正高時,突然一紙調(diào)令又把我調(diào)回到在北京的中央建政文工團(tuán)。我把《克拉瑪依之歌》交給了歌唱家朱崇懋和呂文科,這首由呂文科演唱的《克拉瑪依之歌》第二年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后,很快就傳遍全國,至今已整整傳唱了60年。
那幾年我創(chuàng)作的歌曲題材很多,如《哪兒來了這么一個老貨郎》,好多文工團(tuán)都演過。也有和建筑文工團(tuán)的任務(wù)沾邊的,如《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在也門的晚霞中》《祁連山的回聲》《建筑號子》等等。
2009年6月22日,呂遠(yuǎn)在“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呂遠(yuǎn)八十回響長春音樂會”上致辭。
1963年3月,中央建政文工團(tuán)合并到海政歌舞團(tuán),我穿上軍裝,成為海政歌舞團(tuán)的藝術(shù)指導(dǎo),主要還是創(chuàng)作。海政歌舞團(tuán)給了我很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我經(jīng)常下部隊、下基層,到艦艇上、海島上體驗生活,與官兵們同吃同住同訓(xùn)練。我在海軍創(chuàng)作的許多作品獲得過軍委總政治部或國家的嘉獎,如《毛主席來到軍艦上》《海岸炮兵之歌》《俺的海島好》《水兵最愛什么花》《八月十五月兒明》等等。
1974年1月17日,南越吳庭艷政權(quán)派艦入侵我西沙群島,打死打傷我國漁民,1月19日西沙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打響,我英勇的海軍官兵取得了重大勝利。海軍政治部命令文工團(tuán)立即派創(chuàng)作組到西沙群島慰問及進(jìn)行創(chuàng)作。我和朱祖怡等十位同志奔赴西沙,在那里體驗生活并收集素材。我在琛航島的島礁上撿到一枚我國古代漁民用的銅錢,更堅定了我對南海諸島是祖國神圣領(lǐng)土的信念。在永興島上遇到陸軍榆林要塞的詞作家蘇圻雄同志,相約共同為西沙創(chuàng)作歌曲。隨后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影片《南海風(fēng)云》,我又去海南邀蘇圻雄創(chuàng)作影片的歌詞。這是一次難忘的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的過程。我還順道去通什了解黎族民歌,去儋州研究調(diào)聲,去臨高采集漁歌,收獲頗豐。1976年完成了影片主題曲《西沙,我可愛的家鄉(xiāng)》的創(chuàng)作,由青年歌唱家卞小貞和梁長喜演唱。隨著電影的播放,迅速在大江南北流傳開來。由于廣大人民群眾對南海廣大海域神圣領(lǐng)土的關(guān)注,這首歌曲傳唱多年。幾年前,國家成立三沙市,海南群眾把它改成三沙市歌,我覺得內(nèi)容有點過時,便在三沙市領(lǐng)導(dǎo)的支持下,和蘇圻雄一起創(chuàng)作了《我愛三沙》,由青年歌唱家司紅軍、伊泓遠(yuǎn)演唱,又和肖杰合作創(chuàng)作了《三沙祖宗海》,由楊洪基演唱。這兩首歌曲正在南海的上空飄揚(yáng)著。
“文革”期間,愛情題材已被“砸爛”,在文藝作品里是禁區(qū)。上世紀(jì)70年代末,人民群眾熱切盼望輕松的愛情歌曲。1978年海政歌舞團(tuán)領(lǐng)導(dǎo)大膽地提出要搞一臺輕音樂音樂會。海政文工團(tuán)的詞作家馬金星在沒有人敢突破禁區(qū)的情況下,第一個把《泉水叮咚響》的歌詞放在我面前,我眼前一亮,卻又有點猶豫,因為歌詞描寫的恰恰就是海軍戰(zhàn)士與故鄉(xiāng)戀人間的純潔愛情。這一時期,雖然新的思潮已經(jīng)萌動,但愛情題材仍然是個“雷區(qū)”,歌曲能否被通過,我很有顧慮。但我被這動人的歌詞打動了,在馬金星的鼓勵下,非常投入地創(chuàng)作了這個曲子。《泉水叮咚響》開創(chuàng)了改革開放前的愛情歌曲的先河,卞小貞在工人體育館的冰上音樂會上一唱,很快便風(fēng)行全國。但我清醒地認(rèn)識到,歌曲的流傳與否,不取決于我們作者,也不取決于歌唱家,而是人民群眾,他們需要這樣的歌曲。
1978年初,北影領(lǐng)導(dǎo)決定由謝添導(dǎo)演將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進(jìn)京會演的話劇《甜蜜的事業(yè)》搬上銀幕。我和唐訶同志在1962年同謝添合作過喜劇片《錦上添花》,那部影片很成功,這次北影廠又通過海政宣傳部給我下達(dá)了作曲任務(wù),于是我們就住進(jìn)了北影招待所,開始研究劇本。影片內(nèi)容很好,但里邊的兩首插曲有一首是純愛情內(nèi)容,為強(qiáng)化影片的主旋律風(fēng)格,我們把歌詞給改了幾句,加上了“迎著那長征路上戰(zhàn)斗的風(fēng)雨,為祖國貢獻(xiàn)出青春和力量”以及“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等,主旋律一下子就昂揚(yáng)起來了。對我們搞的音樂伴奏,謝添也嫌我們保守,他要求和當(dāng)時的音樂完全不一樣,對我說:“就那個那個什么,蹦嚓嚓,蹦嚓嚓……”,我知道他是想要舞曲風(fēng)格。經(jīng)過反復(fù)研究,我和唐訶決定寫成三拍圓舞曲節(jié)奏,去找會彈夏威夷吉它的人來錄音,可當(dāng)時“文革”剛結(jié)束,這種人很難找,后來又把中央樂團(tuán)外國剛送來的電子琴用上了,創(chuàng)作了一首非常清新、優(yōu)美的電聲音樂伴奏的抒情樂曲,這就是大家后來聽到的由于淑珍演唱的《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首歌直到現(xiàn)在還在傳唱,并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選成了亞太地區(qū)音樂教材。
上世紀(jì)80年代,已經(jīng)進(jìn)入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接連完成了《紅牡丹》《R4之謎》《玉色蝴蝶》等許多電影作曲,以及《夜幕下的哈爾濱》《愛新覺羅·浩》《木魚石的傳說》等不少電視劇的音樂創(chuàng)作。《牡丹之歌》表現(xiàn)了我們民族不畏嚴(yán)寒、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品格,蔣大為的歌聲充滿昂揚(yáng)的激情,很快風(fēng)靡一時。《有一個美麗的傳說》是電視劇《木魚石的傳說》的主題歌,這個電視劇只有幾集,表現(xiàn)滿清皇帝的老師王爾烈“親民作風(fēng)”的故事,讓我意外的是,電視劇剛播完,歌唱家柳石明演唱的這首歌就“火”了起來,風(fēng)行了30多年,不少男高音歌唱家都唱過這首歌,如蔣大為、閻維文、王宏偉等,就連女高音歌唱家吳碧霞等都作過各具特色的演繹和創(chuàng)新。
在長期的民族音樂創(chuàng)作中,我還積極參加中外音樂交流,特別是與日本音樂界的創(chuàng)作交流活動。我和中國音協(xié)副主席孫慎第一次去日本考察,打開了中日音樂界友好交流的渠道。后來,由日方出資,在中國和日本,由中央歌劇院、海政歌舞團(tuán)和日本青年藝術(shù)團(tuán)的藝術(shù)家合作,在兩國公演了由我作詞作曲的反封建題材歌劇《歌仙——小野小町》,彭沖、程思遠(yuǎn)、賀敬之、曹禺等領(lǐng)導(dǎo)同志出席觀看并給予很高評價。在中日建交15周年、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紀(jì)念時,又重新公演或由中央電視臺播出。我還創(chuàng)作了歌唱中日友好的歌曲,如《世界之愛》《人生之路》等,由中日歌唱家在兩國歌唱。我翻譯的《北國之春》和《永遠(yuǎn)要憧憬》也在中國和日本廣為流傳。從1996年起,我在北京、秦皇島、丹東等地策劃、舉辦了10屆“長城之春國際友好音樂會”,邀請中國、日本、美國的藝術(shù)家到長城下的舞臺上演出音樂和舞蹈節(jié)目,日本的喜納昌吉(周華健的《花心》的原作者)還到八達(dá)嶺上與呂薇一起演唱了他原作的環(huán)保歌曲《花》。
作為一個參加革命70多年、今年已經(jīng)90歲的老文藝戰(zhàn)士,我的黨齡快40年了。我一直覺得黨員是先進(jìn)分子,黨員的要求和標(biāo)準(zhǔn)很高,自己離黨的要求還有差距。我的黨齡不是很長,但我始終認(rèn)為入黨早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時時以黨員的標(biāo)準(zhǔn)嚴(yán)格要求自己,時刻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多年來,我從不參加商業(yè)演出,因為我認(rèn)為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我經(jīng)常想,呂遠(yuǎn)是很渺小的,而黨、祖國和人民的事業(yè)是偉大的,只要能為黨的事業(yè)、祖國的富強(qiáng)和人民的幸福盡到一份責(zé)任,人生就是有意義的。
(慈愛民、劉文韜根據(jù)呂遠(yuǎn)同志口述整理)
中音在線:在線音樂學(xué)習(xí)門戶
相關(guān)內(nèi)容
-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任上海音樂學(xué)院院長2019-1-10
- 葉翠力奪2018中國聲樂藝術(shù)節(jié)青年聲樂藝術(shù)周民族唱法金獎2019-1-9
- 天津音樂學(xué)院2019年本科專業(yè)招生擬錄計劃2019-1-8
- 譚盾:勇敢做自己 完成每一次音樂創(chuàng)作2019-1-8
- 施光南:譜寫改革開放贊歌的音樂家2019-1-8
- 郎朗參與德國國家新年音樂會演奏《黃河頌》2019-1-2
熱點文章
熱門標(biāo)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