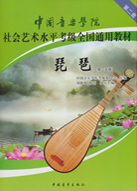形象思維在琵琶演奏中的作用(一)
導語: 形象思維是人類一種最為鮮活和生動的思維形式。琵琶演奏中的形象思維就是演奏者在直覺、心象、想象、投情、設想等思維模式的作用下,將琵琶曲形象、生動地表現出來的思維形式,具有直觀性、具體性和意象性等特點。著名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曾說:“大量證據表明……真正的創造性思維活動都是通過‘意象’進行的”(《視覺思維》)。形象思維以已有的直覺形象來認識和解決問題,貫穿于琵琶演奏過程的始終。 在形象思維的作用下,演奏者首先對樂曲以往演奏情形、音樂形象、樂曲意境等產生具體的、形象的認知。以此為基礎,演奏者不經過邏輯推理就可以敏感地、直接地領會到樂曲的內在情感,這就是直覺。直覺以已經獲得的經驗積累為前提,與靈感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演奏者在內心對看到的、聽到的音樂形象進行總結,形成心象。心象貫穿于演奏思維過程的始末,是一種含有抽象思維因素的形象思維形式。當演奏者大腦中的心象達到一定量時,大腦就會把原有心象的某些部分人為的組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心象,這就是想象。想象是演奏思維的主要活動力量。只有進行充分的想象和聯想,才能正確而充分的投情,這是情感表達最重要的環節。經過直覺、心象、想象、投情等思維模
作者:鄭聰
形象思維是人類一種最為鮮活和生動的思維形式。琵琶演奏中的形象思維就是演奏者在直覺、心象、想象、投情、設想等思維模式的作用下,將琵琶曲形象、生動地表現出來的思維形式,具有直觀性、具體性和意象性等特點。著名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曾說:“大量證據表明……真正的創造性思維活動都是通過‘意象’進行的”(《視覺思維》)。形象思維以已有的直覺形象來認識和解決問題,貫穿于琵琶演奏過程的始終。
在形象思維的作用下,演奏者首先對樂曲以往演奏情形、音樂形象、樂曲意境等產生具體的、形象的認知。以此為基礎,演奏者不經過邏輯推理就可以敏感地、直接地領會到樂曲的內在情感,這就是直覺。直覺以已經獲得的經驗積累為前提,與靈感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演奏者在內心對看到的、聽到的音樂形象進行總結,形成心象。心象貫穿于演奏思維過程的始末,是一種含有抽象思維因素的形象思維形式。當演奏者大腦中的心象達到一定量時,大腦就會把原有心象的某些部分人為的組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心象,這就是想象。想象是演奏思維的主要活動力量。只有進行充分的想象和聯想,才能正確而充分的投情,這是情感表達最重要的環節。經過直覺、心象、想象、投情等思維模式作用后,才可以對演奏情形和過程進行全面的設想,最終將樂曲形象、生動地演奏出來。在這里,形象思維是一個動態的作用過程。
作為一種鮮活和生動的思維形式,形象思維在琵琶演奏和學習中具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運用形象思維去認知和記憶前人的演奏情形,有助于自身琵琶演奏中的情感表現。
琵琶演奏是一種寓個人情感于演奏之中的技巧性表演,其終極目的就是要使演奏者將自身的情感體驗與樂曲所蘊含的情感合二為一,并有所創新與發展。然而琵琶曲是以無聲的樂譜形式保留下來的,演奏者一方面要在抽象思維的作用下對其進行理性認知,另一方面則要在形象思維的支配下去認知前人,認知一些演奏名家或不同派別的演奏情形,尤其是認知一些重要的精彩片斷,并將其記憶下來。當這些音樂記憶痕跡匯集到一定的飽和量時,就會激發起演奏者的內驅力,觸發其靈感,最終把銘刻在記憶中的積累、認知在演奏中更強烈、更集中地傾瀉出來,真正實現樂曲的二度創作。
例如《十面埋伏》是琵琶武曲中最富代表性的曲目之一。琵琶藝術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諸多藝術流派。浦東、平湖、崇明、汪派等不同流派對《十面埋伏》的演奏技法和風格各異,具有各自的特色。我們在學習和演奏前,要對這些流派的演奏音像資料進行反復聽辨和記憶,以獲取更多的情形感受和記憶痕跡,最終為我們自身真實而形象的演奏奠定基礎。如“埋伏”一段,各派在開始的每句處大都作由慢漸快的速度處理,長音大都用“長輪”奏法。崇明派則用“滾”法,加用張力滑音;平湖派采用“長輪”和“劃拂”為主的技法,而浦東派則在長音上用“輪”、“滾”等指法。本段的末尾各派都有長時值音符,表示漢軍千軍萬馬集中到指定地點埋伏下來,準備伏擊楚軍,渲染大戰前特有的寂靜和緊張氣氛。又如“大戰”一段主要表現潰散聲、炮聲、楚歌聲、簫聲、馬嘶聲交織在一起的非凡氣勢。崇明派在本段中運用了“絞四弦”指法;浦東派在這里有馬嘯聲,用了并兩弦同時配“推”、“挽”、“吟”的指法,在本段中部,炮聲與楚歌簫聲間,先用“夾掃”空弦表示奔馳中的馬蹄聲,再在四條弦上做弦數變化的滾奏,這是浦東派善用指法之一:汪派開始用“夾掃”,接著用絞弦與掃輪,描繪戈矢相擊聲,又接炮聲、簫聲以及絞子、中弦、做炮聲時左手指甲須作馬蹄聲。只有對不同派別的演奏情形反復聽辨和記憶,才能汲取各派對自己有用的東西,為自身最終的形象演奏奠定基礎。
(二)在形象思維的作用下,演奏者依次借助直覺、心象、想象、聯想、投情、設想等模式,可以使自身情感與樂曲所要表達的意境完美的融合,最終進行形象的演奏。
借助形象思維,表演者在琵琶演奏中往往會根據樂曲的意境,憑直覺“看”到某種場面,并在內心進行視覺和聽覺感受,形成心象,其后大腦又在原有的心象基礎上加工改造形成新的心象,即進行想象。在此基礎上,演奏者才能調動起心理生活的那種感情,并將其投射到作品所表現的情感世界中去,實現真正的投情。之后,演奏者就可以對演奏的全過程進行生動、具體的形象設想。這是一個動態的作用過程。
相關內容
- 演唱技巧講解2014-10-31
- 《孟姜女》的演唱技巧2014-10-31
- 聲樂基礎:歌唱訓練內容2014-10-31
- 聲樂學習:常見的不良發聲2014-10-31
- 學好視唱練耳需培養音樂感受力2014-10-31
- 視唱樂譜的時兩種唱名法2014-10-31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