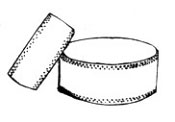朱明瑛:害怕透支赴美國充電 年過六旬仍拼事業
導語: 朱明瑛 攝/法制晚報記者 付丁 制圖/李銘 害怕透支 赴美國充電 年過六旬 仍打拼事業 留洋媳婦 回娘家辦學 1979年的亞非拉歌舞晚會上,朱明瑛涂得一身黝黑走上舞臺,唱起了陌生的扎伊爾歌曲,征服了所有觀眾。 成名之后,她主動學英文、申請出國學習,做著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的事情。1985年,她在美國從零開始,在生意場上打拼。 如今,辦學成為朱明瑛事業的唯一重心。她創辦的北京國際藝術與科學學校,因學費相對低廉,以至于這位61歲的“海歸”藝術家,還需要靠四處“走穴”等方式籌措資金支撐學校。 性格極其要強、精力極其充沛的朱明瑛卻覺得這樣很值,她誓要把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帶到中國

朱明瑛 攝/法制晚報記者 付丁 制圖/李銘
害怕透支 赴美國充電 年過六旬 仍打拼事業
留洋媳婦 回娘家辦學
1979年的亞非拉歌舞晚會上,朱明瑛涂得一身黝黑走上舞臺,唱起了陌生的扎伊爾歌曲,征服了所有觀眾。
成名之后,她主動學英文、申請出國學習,做著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的事情。1985年,她在美國從零開始,在生意場上打拼。
如今,辦學成為朱明瑛事業的唯一重心。她創辦的北京國際藝術與科學學校,因學費相對低廉,以至于這位61歲的“海歸”藝術家,還需要靠四處“走穴”等方式籌措資金支撐學校。
性格極其要強、精力極其充沛的朱明瑛卻覺得這樣很值,她誓要把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帶到中國,并樂于為此奉獻全部。用她的話說,讓她退休做家庭主婦?簡直沒法活了。
愛上藝術 先學舞蹈 26歲改行唱外國歌
FW:您小時候那個時代,多數人的理想應該都是科學家之類,您怎么顯得很另類,要當演員?
朱:我從小酷愛藝術,酷愛藝術的各個門類,這是我骨子里本來就準備好了的。四五歲的時候在大眾劇場看評劇《劉巧兒》,對新鳳霞的表演崇拜至極。
后來我經常找借口跑到劇場的后臺,通過門縫或鑰匙孔去看演員化妝,那時候我就給自己設定好了,將來一定要當演員。如果不讓我從事藝術,我就去死,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
FW:小時候您家里有條件幫您實現夢想嗎?
朱:沒有,那時有錢的孩子都學鋼琴,我家沒錢,學不起。我就趴在窗戶上,看人家學鋼琴,手指頭跟著在窗臺上練習。后來我上舞蹈學校以后成了音樂課代表,是我們班鋼琴彈得最好的。
其實我媽媽特別熱愛藝術,我小時候她常帶我去看電影。當時特別流行印度電影,有時候我聽到誰家傳出收音機播放的《兩畝地》、《流浪者》的舞曲,能冒著大雨站在外邊幾個小時,直到全聽完。
FW:您從小學跳舞,后來改唱歌了?
朱:那時文革剛結束,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都26歲了,不可能在舞蹈上走得更遠。后來鄧麗君的歌進來了,我也接觸了一些載歌載舞的國外的表演方式,我就想試著那樣唱歌。
但那個年代沒人敢說舞蹈演員可以改行,想都沒有人敢想。
我就試著在樂池、幕邊,為跳非洲舞的節目去伴唱,后來樂隊的人說我學音樂要比跳舞更有出息,我一下子有自信了。
FW:您那時怎么想到把自己化妝成黑人,還專唱外國歌?不怕被批判嗎?
朱:我一直就是被批判的對象!我這種沙啞的嗓子,那時候叫喇叭嗓子,在中國聲樂界是不被認可的,說我不配唱歌。那我只好自己找外國歌唱,唱非洲歌曲,周總理當時號召東方歌舞團“學好學像”,我就練到自己聽自己的錄音和原聲都分不出來。
雖然當時批判我的聲音很多,但我意識到中國已經開始改變了,所以沒有犯罪心理,只有冒險心理,而且這種冒險又充滿誘惑力,我本身又是豁得出去的性格,所以愛誰誰了!
離鄉背井 赴美10年 學到了如何經營文化產業
FW:您那時候算是中國內地最前衛的歌手了吧?
朱:那時候沒有“前衛”這個概念。我是半路出家的,就是憑著一股勁豁出去了,什么都不怕。我當時能用26種語言,現在能用31種語言唱世界各國歌曲,我算是中國歌手里積累曲目最多的一個。
我結婚很早,離婚也很早,當時挺痛苦的。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就想,如果讓我選擇要家庭還是要事業,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事業。
FW:后來您決定出國有家庭原因嗎?
朱:沒有。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我雖然不被中國音樂界認可,什么都不是,但卻在老百姓中間火得一塌糊涂,我是自信到那個份兒上才出國的。
而且當時無休止的演出,我也已經透支了,我知道自己該充電了。于是,我先跟文化部要求到非洲學習,人家說非洲沒有音樂學校。后來我去了美國,就奔著有黑人音樂的地方去了。
FW:出國做了什么準備?您外國有親朋?還是有英文基礎?
朱:我決定去,國家同意了,然后我背包就走了。在國外我誰都不認識,就英文還行。唱歌之前我在團里就是一個無名小演員,人家去國外演出就把我當成老弱病殘留下來了,我特別痛苦、失落,沒正事干,就天天學英文。
FW:您沒想到出國后自己根本沒機會演出,沒法從事您摯愛的藝術事業嗎?
朱:我走的時候35歲了,當時覺得自己已經不會再搞藝術了,美國誰也不認識我,誰會看我的演出?我知道去了以后我會很苦,但我是抱著來當學生的心態,不在乎有沒有舞臺。
盡管有心理準備,去了才知道,我還是太狂了,在國內人們那么捧著我,讓我覺得自己很偉大。今天反過來看,還不是因為那時候老百姓少見多怪。到美國后,什么音樂劇、搖滾樂,都是當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藝術門類,美國人的音樂素養真不比我們專業人士差,我覺得自己特別渺小。
FW:我知道您一開始在國外拼命地打工,后來又經商,并未從事藝術行業,其間有沒有無奈?
朱:沒有。我無論干什么都能達到自己的極限,因為我熱愛所有我做過的工作,尤其是它還在未知狀態的時候,我是百分之一萬地要往里鉆。
剛到美國除了要上課外,我還要教中文、跳舞、鋼琴、太極拳,每天至少要打四份工,一直工作到夜里12點多,然后才回到宿舍做功課,但我從來不覺得辛苦。
客觀地講,到了美國我發現,不用說專門學藝術,我隨便走進一個大賣場,貨架上浩瀚的音樂磁帶,一天看都看不過來,生活就是學習。
現在來看,在美國的10年我得到的是我當年沒想到的東西,那就是對經營文化產業的認識。我本來想從美國學習表面上的藝術,但我現在做的文化園區和學校,恰恰是人家骨子里的東西。
回國辦學 邊辦邊賠 61歲仍為事業打拼
FW:1995年回國以后您就開始辦學了嗎?這件事說掙錢也能掙錢,但賠錢的也不在少數吧?
朱:最早做培訓班,后來開始辦學校。真正辦學的,誰說能掙錢?我們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有,除了基本學費,整個過程都不再額外收費。但我們的雙語、藝術、文化課,包括我們的小班授課、國外交流,一切都是與國際接軌……
只要為孩子好的我們都做,只要是掙錢的都跟我們沒關系。所以我辦學當然是賠了,必須賠,從哪兒掙呀?
換一個思路想,我是賠了,但是我看重的是10年以后能出人才,我不看現在。我把我所有的積蓄、演出費、所有賺到的錢都放到辦學上。
這么說吧,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辦學不賺錢,但我要的是未來。辦學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我現在的努力就是為了讓我這個學校未來像清華那樣好。
FW:現在辦學又是您的第一事業了,可您已經61歲了,這么大歲數還為事業打拼,您兒子王玨支持嗎?
朱:從一開始,我兒子就是唯一支持我辦學的人。我到現在也這樣和他說:你不到40歲別結婚,先干事業。他現在不僅自己的音樂事業干得很好,也在和我一同經營學校。
你說我已經到了退休年齡,沒錯。但我就是不能忍受當一個家庭婦女,忍受庸庸碌碌的生活。我一旦離了工作,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使我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永遠有理想,永遠有奔頭。
FW:9月23日“夢回1980”將重現30年前新星音樂會的盛況,您有什么感觸?
朱:當年那場音樂會,我還是剛見婆婆的小媳婦的感覺,一下子被媒體關注,然后忽然被大眾認可。
那時候我演出總是全身涂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擠公交車從來沒人能認出我來,很有意思。到明年我已經從藝整整50年了,時代、心境變化太大了,只有我對藝術的熱愛從來沒變過。 本版文/特稿記者 邵靖
朱明瑛
1950年出生在沈陽;
13歲考入北京舞蹈學校,后進入東方歌舞團成為專業舞蹈演員;
26歲轉行成為歌唱演員;
1979年在中山音樂堂亞非拉歌舞晚會上演唱扎伊爾歌曲《愿大家都成功》;
30歲參加新星音樂會紅透全國;
1985年,赴美國經商;
1995年,回國辦學。
代表作:《愿大家都成功》(扎伊爾)、《愉快的旅行》(黎巴嫩)、《拜斯普薩》(埃及)、《花笠音頭》(日本)、《唱吧,唱吧》(美國)、《猜謎語》(印度)、《我的愛至死不渝》(巴基斯坦)、《回娘家》(中國)。
“夢回1980”演唱曲目
《回娘家》
《萬水千山總是情》
《咿呀呀歐雷歐》
·【專題】第九屆全國聲樂比賽專題報道
· “夢回1980”新星音樂會
· 音樂會主持人闞麗君:獨身至今全心系重聚
· 鄭緒嵐:為愛辭職遇封殺令 情路坎坷病魔奪愛人
· 吳國松:紅透一時來信成山 難登熒屏好嗓子不服
· 王靜:初當新星怕人說閑話 離婚復出宴會上高歌
· 任雁:一夜閃亮十余載雪藏 遠渡重洋洗手做羹湯
相關內容
- 二胡藝術家舒希 “美麗星期天”開音樂會2014-12-3
- 湯沐海 每一次音樂會我都酣暢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適合我,堅持走藝術高端路線2014-12-1
- 昆劇名宿林為林:突破自我再現大將軍韓信2014-12-1
- 裴艷玲正籌備新戲《漁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現“老普”音樂的放肆之美2014-11-27
熱點文章
熱門標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