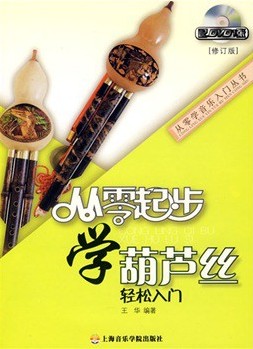“無孔不入”的杜聰(二)
導語: 一個普通人,聰明,有點天分,不執著,不死磕,在命運的水流中順勢而動,于是尋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杜聰從他的臥室里取出一把排簫,用袖子撣撣簫身,然后嘴唇在上面“唰”地拭擦一下,吹出了一串音。這樣的試音甚至讓人想到了一個屠戶拭擦他手中的刀,鐺的一聲,嫻熟又充滿了人間煙火。 “排簫與其他樂器相比,它究竟好在哪?” “能說清楚的都不是好音樂,要聽。”杜聰說。 “為五斗米折腰” 杜聰成名于排簫。1991年,他灌制了第一張排簫唱片——《沉思》,獲得了第三屆中國金唱片獎。從此,他成為口碑一致的“排簫王子”,亞洲排簫第一人。迄今,杜聰已經錄制了100多張CD,國際上風靡的《阿姐鼓》《央金瑪》《蘇武牧羊》里面,都有他的排簫聲。可杜聰始終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時時要面對生存壓力的藝人。 從上海音樂附中開始,杜聰一直專修笛子。而他出生的城市“崇洋”,民樂只能地處邊緣。1978年,杜聰進入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時,雖然是當時上海考區中惟一錄取的民樂系學生,但四年里別人還一直以為他是鋼琴系的。因為他一直是把笛子藏在袖子里,手里揚著鋼琴譜,昂首
講這個故事時,杜聰的語調很平淡。但這話讓人覺出些他藏在心底的光榮。這種光榮不是在心里呼號著一個崇高的藝術理想,或者一種曠絕古今的演奏境界。而是一個不喜歡和命運死磕的人,在命運的水流中順勢而動,用自己的頭腦和“小花招”,找到出路的驕傲。
“我都有辦法”
1993年,杜聰參加了《阿姐鼓》的錄制。那是最愉快也最無局限的一次創作。如果玩不出新鮮感,3500元/天的錄制棚就歇著等。在90年代初,這對走非流行路線的音樂人來說已經是種奢侈。“那一次我知道了,好音樂是玩出來的。”杜聰說。
杜聰說,他經歷過很多難以應付的場合,但總可以玩出些“小花招”渡過難關。
曾經因為頻繁走穴,杜聰被上海民族樂團發配到一個縣城的小樂團去演出,杜聰在那里發明了單手吹口笛的方法。“因為團里缺節目,我就想了這么個小花招。一只手彈電子琴,一只手吹口笛。”回到上海民族樂團后,杜聰憑這個“小花招”,從第八位笛手,升到了第二位。
1996年,杜聰第一次在北京開演奏會,演奏會一個星期前,發現邀人寫的三首曲子都不能用。他靠著一開場就秀自己獨創的玻璃瓶吹奏,舉座皆驚。
去臺灣演出,杜聰的新花招是比較少見的樂器——弓笛,并在弓箭一樣彎曲的笛身,第一次用一把笛,一個人,吹出了雙聲部。“其實,雙聲部是由嗓子輔助的。”雖然喉嚨一邊發聲一邊吹奏,而且兩邊要相得益彰,是個不容易的事情,但杜聰寧可把這說成自己耍的“雕蟲小技”。
現在的杜聰,似乎再不用像當初在希爾頓飯店走穴時那樣為出路發愁了。他是很多電影導演錄制片中音樂的首選,還有著不間斷的錄音邀請。
杜聰還有個綽號叫“無孔不入”——所有有孔的吹奏樂器,他拿在手中擺弄一會就可以演奏。采訪時,他排出他的樂器,鋪在沙發,茶幾,凌亂的十幾平米空間的所有間隙處,再一個個吹奏出來。秘魯的排簫,印度的笛子,泰國的竹器,墨西哥的陶制人塤,歐洲的豎笛,古老的弓笛,信手拈來。
對所有學藝的苦練,他幾乎都談得都非常淡。傳說中,練習吹奏樂器,嘴唇會被竹子磨破幾層皮。他說他有辦法:在竹管的下方,塞進一團沾滿油的棉花,吹的時候蘸一點油抹在排簫的吹口處,“這樣磨損就小多了。”他得意地笑了。杜聰就是這樣得意于自己的每次“小聰明”,每個小創造。
但是對杜聰來說,排蕭并不能管他一輩子。輕音樂界每天都在上演著“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的戲劇。排簫滅了情調鋼琴,薩克斯替代了排簫,陳美的瘋狂小提琴又顛覆了薩克斯,現在火的是“十二樂坊”,那種人多勢眾的民樂大合奏。
“理查德·克萊德曼已經到溫州的鄉下做表演了,排簫也已經賣得不好。”說起別人的走向邊緣和排簫的“失勢”,他都一樣嘻嘻笑著,“不過,我都有辦法。”
現在杜聰又開始吹塤,“因為現在古怪的民間樂器受歡迎了。”家里客廳的長沙發頂上排了一溜各種尺寸的塤。從一種大眾潮流轉向另一種,就好像轉個身那么簡單。如臺灣導演張艾嘉說,做導演不是在拍戲,而是在解決問題。而高明的導演,對所有的問題,“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杜聰對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也是:“適應能力很強。”這是他對自己不多的正面評價之一。(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相關內容
- 二胡藝術家舒希 “美麗星期天”開音樂會2014-12-3
- 湯沐海 每一次音樂會我都酣暢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適合我,堅持走藝術高端路線2014-12-1
- 昆劇名宿林為林:突破自我再現大將軍韓信2014-12-1
- 裴艷玲正籌備新戲《漁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現“老普”音樂的放肆之美2014-11-27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