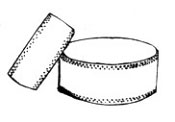肖邦年真實的肖邦:那些被渲染的和被遮蔽的
導語:簡要內容:作為一名出入于巴黎貴族沙龍中的音樂家,肖邦擅長將個人傳奇與公眾形象融合得水乳交融。肖邦的作品有鋼琴協奏曲兩部,鋼琴奏鳴曲三部以及瑪祖卡等,曲調多樣,和聲優美,動人心弦。 所謂歷史,難免有后來記述者一廂情愿的成分。音樂史也不外乎如此。更何況是對200年前的肖邦——這樣一位將大眾的傳奇、離奇的緋聞和耐人尋味的音樂交織于一身的人物。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肖邦。他也許是那位用琴鍵編織著夢幻的作曲家,也許是那位臨死前仍高呼“把我的心臟運回波蘭”的民族主義斗士,也許是那位出入于巴黎高級沙龍、神經兮兮卻分外得寵的公眾藝術家,也許是那個著名情人喬治·桑筆下極盡溫柔之能事的“我親愛的小肖邦”。 可以確信的是,出現在后世音樂史冊或電影、小說等文藝作品中的那個肖邦總是在被一代又一代追隨者所誤讀和塑造。他的昂揚、悶騷、孤獨和詩
簡要內容:作為一名出入于巴黎貴族沙龍中的音樂家,肖邦擅長將個人傳奇與公眾形象融合得水乳交融。肖邦的作品有鋼琴協奏曲兩部,鋼琴奏鳴曲三部以及瑪祖卡等,曲調多樣,和聲優美,動人心弦。

所謂歷史,難免有后來記述者一廂情愿的成分。音樂史也不外乎如此。更何況是對200年前的肖邦——這樣一位將大眾的傳奇、離奇的緋聞和耐人尋味的音樂交織于一身的人物。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肖邦。他也許是那位用琴鍵編織著夢幻的作曲家,也許是那位臨死前仍高呼“把我的心臟運回波蘭”的民族主義斗士,也許是那位出入于巴黎高級沙龍、神經兮兮卻分外得寵的公眾藝術家,也許是那個著名情人喬治·桑筆下極盡溫柔之能事的“我親愛的小肖邦”。
可以確信的是,出現在后世音樂史冊或電影、小說等文藝作品中的那個肖邦總是在被一代又一代追隨者所誤讀和塑造。他的昂揚、悶騷、孤獨和詩意,都被不同程度地渲染;他的傲慢、怯懦、軟弱和神經質,則被有意無意地遮蔽掉了。
不同的時代,按照不同的需要塑造著“應該是”的那個肖邦。他原本的形象卻已經四分五裂,模糊不清。在這位音樂巨子誕辰200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盡可能地撥開迷霧,認識一個作為矛盾綜合體的真實肖邦,以及他背后那動機復雜的偉大音樂。
“花叢中的大炮”受質疑
“藏在花叢中的大炮”,這句出自同時代音樂家舒曼之口的名言,成為貼在肖邦及其音樂身上最著名的標簽。警句式的語言富有煽動色彩,語氣中又伴著不容置疑的態度。然而,后代的許多研究者發現,這個最受媒體歡迎的句子固然非常著名,但卻并非最準確。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肖邦的音樂,難免會受到誤導。
肖邦年少成名,后半生以波蘭亡國為由,在“花都”巴黎度過余生。在人們常見的宣傳資料中,很容易找到他嚴詞拒絕沙俄授予他“俄國皇帝陛下首席鋼琴家”職位的字眼,而他曾經參加過反抗侵略者的起義也被特別渲染。尤其是肖邦在流亡之前要求帶走“一捧故鄉的泥土”,以及死后“把我的心臟運回波蘭”的故事,更是讓一個作為絕對民族主義者的肖邦形象流傳世界。也成為慣于激動的舒曼“花叢中的大炮”一說的主要依據。
然而,這些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故事卻受到不少肖邦身邊人士、當事人和嚴肅歷史學家的質疑。肖邦自己曾表示:“我沒有參加華沙起義,是因為我當時太年輕,但是我的心是和起義者在一起的!”可見肖邦離開華沙投奔巴黎的直接原因并非他身為起義者所受的迫害,而是有別的原因。我國研究者唐若甫指出:“與浪漫電影展現的‘花叢中的大炮’不同,肖邦并非民族英雄般的人物。病痛和流離或許能為他博得同情,但肖邦逃避波蘭并非支持革命,而是遺棄革命。”
作為一名出入于巴黎貴族沙龍中的音樂家,肖邦擅長將個人傳奇與公眾形象融合得水乳交融。1839年,肖邦自己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是一個蘑菇,看上去可食,但若你膽敢采下咽去,蘑菇便會毒性大發。”肖邦所景仰的流放詩人亞當·米基維茨對自己的這位追隨者頗為不齒,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肖邦有著對祖國見風使舵式的懷念和對貴族社會阿諛奉承的天性,指責肖邦為“道德吸血鬼”。
目前所見史料中,有關肖邦民族主義壯舉的最早報道,大多來自當時沙皇俄國內部革命派的報刊和前蘇聯的宣傳刊物中。他們竭力渲染著肖邦的民族情結,并強調著肖邦音樂中的民族性。這些來自俄國的力量介入,才讓肖邦在遠離波蘭多年后,重新被波蘭人認識。以至于肖邦去世之后,俄國音樂家巴拉基列夫滿懷熱情地探訪肖邦出生地時,驚訝地發現當地人根本不記得有過這樣一位天才。通過俄國人的努力,肖邦紀念碑才在其出生的小鎮豎立。
肖邦故事的不可靠性并不影響其音樂的偉大。然而,后代的許多演奏者按照“花叢中的大炮”的指引去揣摩和演奏肖邦的音樂,卻引起了很多爭議。很多人以為,彈肖邦的作品一定要激情、奔放、浪漫,甚至無拘無束地將其音樂彈得那樣火熱、燦爛、輝煌。這是否就一定是作曲家的本意?
當代音樂家巴倫博伊姆就對這種一廂情愿的解讀不以為然。他認為肖邦固然有著自然而然的民族情結和愛國情懷,但許多文藝化的故事顯然將其渲染得過于理想主義。肖邦的音樂與附著在他身上的那些故事并不能簡單地畫等號:“他是一個幾乎從不直白表露自己情感的人,其深藏不露,與李斯特的張揚截然相反。他理性,不會過度激情。許多人以為他跟古典主義水火不容,實際上,肖邦是浪漫主義時期中最古典的一位。”
詩情畫意的甜蜜偽裝
在無數星級酒店那光可鑒人的旋轉門背后,肖邦的鋼琴曲總是最恰切的背景音樂。在如今這個時代,肖邦這個名字似乎總與高貴、優雅、閑適和不落俗套聯系在一起。在許多流行文化中,如周杰倫的專輯《十一月的肖邦》和電影《不能說的秘密》里,肖邦的音樂被有意無意地“中產化”了,成為消費主義時代的溫情標簽。所涉作品尤以肖邦的夜曲為甚。
肖邦被稱為“鋼琴詩人”。他寫出的音樂也確實具有詩的特質。尤其是夜曲題材,雖然并非肖邦首創,然而他卻在繼承其創始人菲爾德古典結構的基礎上,將美聲詠嘆調的旋律和氣息融入其中,令夜曲具有了浪漫的美感。這些夜曲極富肖邦的個人特質,旋律悠長深廣,裝飾精美,在表現手法上自由舒展,變奏手法精細,似中國山水畫中自由自在的線條藝術,迷人的旋律中滲透著一種甜甜的傷感。
這種詩情畫意,為肖邦的夜曲音樂披上了一層甜蜜的偽裝。然而,假如只沿著這樣溫情脈脈的路線去演繹肖邦,那就大大限制了音樂的格局。肖邦音樂中的戲劇張力往往被人們所忽略。尤其是他所采用的和聲語匯,帶給了音樂最深沉的力量。雖然,這與人們一般印象中的舒適、柔緩、催情等俗套背道而馳,然而它卻是肖邦音樂中最具價值的部分。
肖邦曾說,他不喜歡沒有內在思想的音樂。確實,即使在最抒情的夜曲中,他的情感濃度也咄咄逼人。而在敘事曲和奏鳴曲里,肖邦更呈現出戲劇化的一面,這些作品不同段落間的對比非常強烈,引入了許多戲劇沖突般的聲音元素。
被公認為肖邦權威演奏者的著名鋼琴家波里尼的演奏便與眾不同,音符嚴謹清晰,自由速度用得很小心,卻別具魔力。波里尼認為演奏肖邦首要是表達出音樂中的偉大與深刻,體現出“悲劇式的崇高”,他認為肖邦的夜曲完全有資格站在這個高度。
在肖邦的音樂肖像上,被涂抹了太多柔弱、甜美的浪漫特色,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流行歌手將它改頭換面、作為專輯主打的原因。然而,只有撕下這層裹了蜜糖的偽裝,才能真正讀得懂他的寂寞,聽得懂他的彷徨。
愛情是源泉 更是傷害
與作家喬治·桑的那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成為肖邦后期音樂創作的當然背景。不可否認的是,與喬治·桑長達9年的愛情生活,是肖邦音樂創作最勃發的時期,愛情成為他靈感的源泉。然而,肖邦對性格強悍的喬治·桑在情感方面強烈的依附性,也使他的心靈更加敏感孱弱,音樂趨于沙龍化,并造就了他分裂的人格,曾經健康活潑的音樂主旨隨著情感的枯竭而漸漸流逝。
一般的男女戀情,通常男如火,女如水。然而在肖邦和喬治·桑的姐弟戀中,這種關系顛倒過來了。處于主動地位的喬治·桑總是熱情如火,從外鄉來到巴黎、寄居喬治·桑門下的肖邦反而柔情似水。這種曲折而變異的情感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肖邦的創作路線。可以說,在相當長時間里,肖邦進行音樂創作的自主性并不強。他的才華在得到喬治·桑滋養的同時,也被套上了一根柔軟的繩索。
看看,剛剛從被當時的西歐人視為“鄉下”的波蘭來到巴黎的肖邦是怎樣一種形象:在喬治·桑家的客廳里,浪漫主義藝術大師德拉克洛瓦為肖邦畫過一幅肖像,畫上的肖邦消瘦憔悴,詩人波德萊爾譏誚說肖像上是“一個已經摸到棺材的人”。那時的肖邦得了嚴重的肺結核,臉色蒼白,柔弱多病,但舉止文雅。詩人海涅說他有“一個柔弱、勻稱但有一點病態的身材,以及高貴的心和天才”。
文弱俊美,蒼白而略有病態,高貴且才華橫溢,讓肖邦具備了讓巴黎上流社會婦女憐愛的條件。而那時的喬治·桑卻愛穿男裝,藐視傳統,飲烈酒、抽雪茄、罵起人來滿口污言穢語。她的顯赫地位和對肖邦的傾慕與推崇,足以使肖邦得以在當時巴黎藝術家成名的唯一捷徑——貴族沙龍中如魚得水。就這樣,雌性化的肖邦與雄性化的喬治·桑令人驚訝地走到了一起。肖邦擁有了情感寄托和相對安逸的生活,從而迎來創作力最為旺盛的時期。
很少有人知道,肖邦的外表與他的內心世界反差非常大。就連與肖邦共同生活了許多年的喬治·桑,也未必能真正理解肖邦,她說:“肖邦是一朵玫瑰花的葉子,蒼蠅的陰影擋住了射在玫瑰花上陽光,使肖邦呈病態、失血,乃至身亡。”喬治·桑顯然認為肖邦從軀殼到靈魂都是病態的,她在與肖邦的關系中充當的是情人兼母親的角色。
肖邦的本質是在他寫的一系列波羅乃茲舞曲中顯現出來的。那些有著巖漿般熱情的樂曲是肖邦內心的真正釋放,成為肖邦音樂的最高成就。然而,在大多數時候,他都忍受著內心的苦楚和折磨。他的更多作品都在副標題上注明“獻給某某夫人”。他甚至承受不住與喬治·桑關系中的壓力,從而與喬治·桑的女兒有了不倫之情。此時,喬治·桑那種霸道的愛對肖邦及其音樂已經成為傷害。
這就是兩個世紀前的真實肖邦。杰出與渺小并存,天才與虛榮兼具,堅強和軟弱呈現在同一個人身上。要想從他的人生去理解他的音樂,線索是如此復雜。然而,也許這才是偉大音樂的魅力所在。
肖邦
(CHOPIN,1810-1849年)出身于教師家庭,六歲開始學琴,八歲首次演出,轟動華沙,被譽為“波蘭的莫扎特”。1826-1829年在華沙音樂學院深造。1830年定居巴黎,從事創作和教學。1849年在巴黎逝世。肖邦的心臟現安放在華沙圣十字教堂。肖邦的作品有鋼琴協奏曲兩部,鋼琴奏鳴曲三部以及瑪祖卡等,曲調多樣,和聲優美,動人心弦。
來源:中國經濟網
相關內容
- 二胡藝術家舒希 “美麗星期天”開音樂會2014-12-3
- 湯沐海 每一次音樂會我都酣暢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適合我,堅持走藝術高端路線2014-12-1
- 昆劇名宿林為林:突破自我再現大將軍韓信2014-12-1
- 裴艷玲正籌備新戲《漁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現“老普”音樂的放肆之美2014-11-27
熱點文章
熱門標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