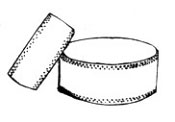鄭小瑛——女性同樣能在指揮陣地上打好仗
導語: 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鄭小瑛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指揮界獨樹一幟。在三八婦女節來臨之際,本報記者就女指揮家所處境地及面臨的問題,對鄭小瑛進行了專訪。 性別歧視一直存在 記:有人說女性不適合站在指揮臺上,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鄭:要看是誰了,不要籠統的講。在音樂界性別歧視一直就有,像卡拉揚樂隊的一個女黑管都鬧了那么大的風波,何況是指揮。指揮本來就是男人的崗位。當我出現在西方人面前,他們很驚奇。因為當時熱播的電影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這些,中國女性在西方人心中基本都是那些電影中的形象,而我這樣一副“呼風喚雨”的樣子讓他們很難相信我是中國人。 2002年底,我到美國威斯利安大學講學,很多美國女研究生寫信給我,說我給了她們很多啟發。她們說從我身上期待很多個人奮斗的故事,但是我告訴她們我沒有那么多傳奇經歷,我的領導看我有一定才能,能把工作完成得好,機會來了就送我

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鄭小瑛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指揮界獨樹一幟。在三八婦女節來臨之際,本報記者就女指揮家所處境地及面臨的問題,對鄭小瑛進行了專訪。
性別歧視一直存在
記:有人說女性不適合站在指揮臺上,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鄭:要看是誰了,不要籠統的講。在音樂界性別歧視一直就有,像卡拉揚樂隊的一個女黑管都鬧了那么大的風波,何況是指揮。指揮本來就是男人的崗位。當我出現在西方人面前,他們很驚奇。因為當時熱播的電影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這些,中國女性在西方人心中基本都是那些電影中的形象,而我這樣一副“呼風喚雨”的樣子讓他們很難相信我是中國人。
2002年底,我到美國威斯利安大學講學,很多美國女研究生寫信給我,說我給了她們很多啟發。她們說從我身上期待很多個人奮斗的故事,但是我告訴她們我沒有那么多傳奇經歷,我的領導看我有一定才能,能把工作完成得好,機會來了就送我去學習,學習優秀就委以重任。新中國在知識分子階層沒有性別歧視,因此我的職業道路很順利。
記:那么據您所知國外的女指揮家的境況如何?
鄭:1987年,我去拜訪美國的一個女指揮安東尼奧·布里克(Antonia Brico),當時她已經80多歲了,她坐在沙發里面不能站起來了,但目光很有神。她見我第一句話就問:“你們中國有沒有歧視女指揮?”我說:“沒有,我是中國國家歌劇院的首席指揮,同時也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她說:“你非常幸運。在美國,人們對女指揮有很深的成見。”我當時還不大明白,但是后來布里克去世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國朋友寄給我的登載布里克辭世消息的報紙,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一個沒有被認識的天才》,上面說如果她是個男性,她應當屬于世界一流。我這才知道她在世時為什么心里這么委屈和抱怨,她曾經指揮過柏林愛樂,也指揮過紐約愛樂,但她從來沒有在一個重要樂團當過總監,只當過客席。美國的一些婦女協會(通常是一些很有錢的寡婦)出資為她組建了一個散裝的樂隊,表示對她的尊重和支持,僅此而已。所以相比較而言,我感到很慶幸。
記:當年您去蘇聯留學的時候,女音樂家的情況是怎樣的?
鄭:我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時候當時沒有女生,后來在列寧格勒,有一個女生跟我抱怨說:“我將來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只能到西伯利亞去了”。有一次我的老師安諾索夫帶我去見他的女學生杜達洛娃(Du?鄄darova),她是蘇聯的第一個女指揮,她向老師打趣說:“您不是再也不招女學生了嗎?怎么又招了一個?”老師說:“這個不一樣,她是從中國來的,她很有才華”。后來我問老師為什么不教女學生了?他說因為培養一個指揮,國家要付出很多,但是在蘇聯,女性一般結婚后就不再出來工作了,所以是一種浪費。
女性必須更加優秀才有機會
記:和男性相比,女性音樂家在事業上會有哪些優勢嗎?
鄭:從承擔的任務和專業條件上來說,男性和女性應該說沒有什么不同,在音樂上是沒有辦法區分男性女性的。在樂隊面前,演奏員不會因為你是女性就會降低對你的要求,容忍你的失誤或者無能,倒是更加容易挑剔。我常對西方的記者講,我的成長中間沒有受過性別歧視,但也沒有受過性別優待,從來沒有因為國家要樹立形象之類的,去安排一個女指揮家,不會這樣。
但是,女指揮需要克服更多生理上的特殊困難,特別是婚后往往被家庭和孩子拖累,總不能因為你家庭不和或者孩子生病,就讓樂隊與合唱隊的幾十、上百人等著你吧?指揮白天要排練,晚上要準備總譜或演出,這就需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堅強的毅力和寬廣的胸襟,要有足夠的自信,工作不能優柔寡斷。因此,我在挑選女學生的時候往往更加看重她們的性格,然后才是素質的考察。
記:現在如果有女生想學指揮,您對她們有些什么建議?
鄭:我在中央音樂學院作系主任的時候對女生是平等的,當時和我同事的幾位老師還多少有一點偏見。有些女生是很優秀的,像張弦(現為紐約愛樂樂團副指揮)、郭爽(后來赴德學習,曾在芬蘭西貝柳斯國際指揮比賽中獲獎)、金成華(本科畢業后赴德深造,在德國的歌劇院任音樂指導)等等。
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優秀的女生越來越多,沒辦法不收她們。在學校里是這個行情,也許將來有一天在指揮臺上也會呈現這個現象。只要女孩子優秀、努力,沒有男的比她們強,為什么不用?中國女性正因為傳統受壓,所以性格中有一種韌性,不怕壓制,不怕困難,有一種事業成功的追求。
但是現在就業確實非常難,也有許多優秀的女孩來找我想學指揮,我先給她們潑冷水,我說現在出去是找不到工作啊,除非你比所有的男人都強。我那個年代比你們現在好,那個時候沒有性別歧視,要有這種思想準備。但她們執著得不得了,而且很多人要以我為榜樣。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社會很多歧視婦女的東西傳進來了。現在一個女指揮,除非她特別優秀、特別出類拔萃才可能有機會。
女音樂家并不都是小肚雞腸
記:當時創建“愛樂女”的時候是不是也是想為女性音樂家創造一些機會?
鄭:其實當時并沒有刻意去這樣想,就是覺得市場經濟對嚴肅藝術沖擊很大,樂團都不演出了,演員們要么去鉆棚錄音、要么去走穴賺錢,學生們就知道鄧麗君,也沒人聽交響樂了。我和司徒(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朱麗(總政歌劇團首席)湊到一塊偶然說起這個事情來,覺得大家都不上班了,就是在家做飯、看孩子,能不能找一些賦閑在家的女樂手,搞個小樂隊去學校演一演,介紹點室內樂之類的。于是她們就打電話聯絡,結果第一次排練,居然來了十幾個人。當時我們高興壞了,很受鼓舞,因為之前說好是沒錢的。我們幾個都是女的,就起了“愛樂女”這個名字,當時就覺得女的是不是能好說話一點啊,大家也都很喜歡,于是就這樣叫開了。
現在回想起來,“愛樂女”是一個非常可愛的集體,大家到了一起都很親熱,說的都是演出排練的事,沒有人提錢。女音樂家不是人人都小肚雞腸,女音樂家也有非常大氣的。通常來講,男性覺得好像要陽剛,女的比較柔和,但也不一定,男性中也有很抒情的,甚至是很脆弱的,相反女性中也有比較剛毅的,這是個性問題,不能以性別來區分。因為沒有錢,所以看重錢的人就不來了,來的都是愛藝術的、性格開朗的、不太在乎的。當用一種理想來團結大家的時候,會有一些人走到一起來,我們在7年中演了300多場,不容易啊,都是不計報酬的。后來有人給我們捐一些錢,也無非就是交通補助啊之類的,現在想來真的很感動。
相關內容
- 趙季平:我們就像王昆老師的子女 內心深深尊敬她2014-11-24
- 評論:王昆,“倔強”的老太太2014-11-24
- 陳維亞:為京劇注入歌舞元素 不能喧賓奪主2014-11-24
- 聲樂泰斗樓乾貴逝世2014-11-24
- 周戰政:“學音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學做人”2014-11-24
- 袁東艷12個劇種輪番唱2014-11-23
熱點文章
熱門標簽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