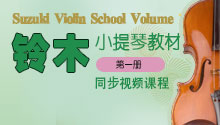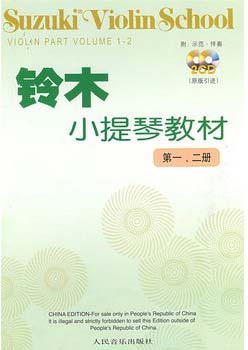馬勒的百年“復活”之路
導語: 楊燕迪 在一位音樂家百年忌辰的時刻談論他的“復活”,不免有種異樣的感覺。須知,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 年)終生縈繞于懷的命題正是“死亡”與“永生”的矛盾糾結。如果馬勒地下有靈,聽到全世界在自己肉身離世百年之后依然津津樂道于自己筆下的音樂,嘴邊或許會露出一絲神秘的微笑——這一事實正好說明藝術的意義所在,它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物質性的死亡和湮滅,從而獲得象征性的永生與永恒。 “復活”故事 有意思的是,馬勒身后確乎真真切切經歷了“復活”的奇跡——與其他許多在世時就獲取名望、贏得尊重的作曲家不同,馬勒在世時及去世后半個世紀中,不僅少有人視其為重要的藝術創作家,而且很多人(包括諸多知名的音樂人)甚至認為馬勒是一個根本不夠格的乖僻作曲匠——不錯,馬勒生前有極高的藝術聲望和顯赫的社會地位,但那是作為一個指揮家,一個從事“二度創作”的表演家。但是,奇跡開始發生并快速“顯靈”。自1960年代開始,隨后至今五十年中,馬勒從一個處于音樂創作史邊緣區域的、地位曖昧的“小作曲家”,逐漸走向樂壇的“中心”,不僅贏得專家的認可和推崇,更
楊燕迪
在一位音樂家百年忌辰的時刻談論他的“復活”,不免有種異樣的感覺。須知,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 年)終生縈繞于懷的命題正是“死亡”與“永生”的矛盾糾結。如果馬勒地下有靈,聽到全世界在自己肉身離世百年之后依然津津樂道于自己筆下的音樂,嘴邊或許會露出一絲神秘的微笑——這一事實正好說明藝術的意義所在,它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物質性的死亡和湮滅,從而獲得象征性的永生與永恒。
“復活”故事
有意思的是,馬勒身后確乎真真切切經歷了“復活”的奇跡——與其他許多在世時就獲取名望、贏得尊重的作曲家不同,馬勒在世時及去世后半個世紀中,不僅少有人視其為重要的藝術創作家,而且很多人(包括諸多知名的音樂人)甚至認為馬勒是一個根本不夠格的乖僻作曲匠——不錯,馬勒生前有極高的藝術聲望和顯赫的社會地位,但那是作為一個指揮家,一個從事“二度創作”的表演家。但是,奇跡開始發生并快速“顯靈”。自1960年代開始,隨后至今五十年中,馬勒從一個處于音樂創作史邊緣區域的、地位曖昧的“小作曲家”,逐漸走向樂壇的“中心”,不僅贏得專家的認可和推崇,更是獲得廣大愛樂者的青睞與喜愛,由此搖身轉變為具有重大藝術意義和突出音樂價值的“大作曲家”。
這一“復活”故事果真富于戲劇性,是否顯得蹊蹺?馬勒生前歷任布達佩斯歌劇院院長、漢堡歌劇院院長,更有十年之久身居維也納歌劇院院長和藝術總監的高位,作為指揮家和管理者權重一時,但他的創作理念和風格路線在其生前和身后都遭人詬病。一方面,馬勒的音樂遠不如同代的德彪西、理查·施特勞斯、斯克里亞賓等人那樣“前衛”,一直固守交響曲、藝術歌曲等德奧音樂的傳統陣地,也難得在音樂語言的拓展和發明上有“激進”之舉;另一方面,他的音樂寫作和敘述往往又不符合藝術音樂的正宗審美標準,尤其是違背從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等人傳至勃拉姆斯的德奧音樂衣缽:統一、凝練、邏輯、連貫——馬勒某些音樂的表象特征恰恰是上述范疇的反面:混雜、扭曲、散亂、斷裂。那么,我們不禁發問,在這個馬勒“復活”的故事進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
“復活”緣由
任何文化現象的產生,必定有其深刻的社會心理根源。一句似已成為眾人口頭禪的名言來自著名哲人黑格爾:“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馬勒的“復活”同樣如此。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為何馬勒“復活”的時間不早不晚,恰在上世紀60年代?
站在當前的有利視角回望五十年前,明眼人察覺,1960年代正值西方所謂“后現代”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思潮的形成期——據稱,其主要特征為中心消散、價值多元,啟蒙時代以來的邏輯和理性遭到懷疑,至高的權威和共享的理想一去不返。這時的藝術空氣中彌漫著某種迷茫而又混亂的氣息,而在音樂中,現代主義的理性推進和語言探索在此時走入死路,放肆的實驗和激進的拓展在此后則成為強弩之末。路在何方?多元和混雜正是時代的基調。
馬勒的音樂特質如榫卯交合般奇妙地與這個“后現代”的時代感覺相匹配。于是,馬勒被“重新發現”,并因此“復活”。當“60后”以及“70后” 乃至“80后、90后”的音樂中頻頻出現“拼貼”、“引錄”以及“多元風格”的手法招數時,人們驚訝地發覺,馬勒的音樂實踐早已做出了大規模的預示。進一步,人們在馬勒音樂中聽出了更多的時代預告——戰爭機器的兇暴、現代生活的焦慮、哭笑不得的窘迫,以及對逝去時光和美好彼岸的懷舊與感傷。馬勒對自己曾有精確的預言——“我的時代終會到來。”看來,馬勒已經預感到人類將在20世紀遭遇的險惡困境并將這些感受真切寫入音樂。他甚至預知自己必將“復活”。
反諷與悲愁
而“復活”的渴望確乎貫穿馬勒一生。他的《第二交響曲》即以“復活”冠名,試圖通過塵世的磨難,最終在基督教“啟示錄”的末日審判和來世至福中安頓身心。但身處百年前的“世紀末”,馬勒在目睹西方社會進步的同時,深刻感到了人類精神信仰的動搖與前途命運的不測。這是一種悲喜參半、正反交疊的獨特體驗,而他的人生親歷恰是這種體驗的催化劑:一方面,他步步青云,指揮事業發展順利,受到萬眾矚目,后又迎娶維也納著名美人阿爾瑪為妻,真可謂春風得意;另一方面,身為外鄉猶太人,他時時感到身份危機,心系創作,但又往往難以騰出時間,加之親人不斷亡故離世,夫妻間后來又常起齟齬,真令他感到心力交瘁……
藝術家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他能將某種深刻的世界體驗與生活態度化為可感、客觀的藝術形式,并將其塑造為圓滿與成熟的風格范疇,從中我們會聽到某種獨特而醒目的“人格聲音”——只屬于他個人,但又具有普遍意義。馬勒音樂中所獨具的“人格聲音”是他悲喜交加的矛盾人生的音響寫照,其中最獨特的表現范疇是尖利的反諷與刻薄的嘲弄。音樂史中,“正話反說”的刻意諷刺并非沒有先例,但達到如馬勒這般深入、尖銳且大面積滲透程度的卻前無古人。《第一交響曲》的第三樂章,在一個貌似悲哀的葬禮行進中,突然傳來木管的嬉笑,緊隨其后的像是一支粗糲而歡快的鄉間管樂隊——這里的音樂安排初聽幾近“無厘頭”,但卻道出生命中的幾多荒誕與乖張。進行曲,原本是勝利與凱旋的音響代表,在馬勒手中要么成為壓抑的異化信號(藝術歌曲《起床號》、《小鼓手》),要么干脆變得猙獰、兇惡而面目可憎(《第六交響曲》)。康健的鄉間連德勒舞曲或者儀態優雅的圓舞曲,在馬勒的交響曲中經常被作為“諧謔曲”的替代,但由于加入了奇怪的不協和音響或配以奇異刺激的音色,似乎都帶有了不祥的預兆,魑魅魍魎的鬼影不時閃現。
但在進行深刻反諷與無情嘲弄的同時,馬勒又是一個帶有典型浪漫主義情懷的懷舊者與企望者。人到中年后,他的旋律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感傷情調,有時甚至帶著病態的渴望與沉痛的呻吟。基于德國著名文人呂克特詩作的聲樂套曲《亡兒之歌》專門寫喪子的生者對夭折孩童的悲悼與思念,只有真正親歷過生死離別的人才寫得出這份深入骨髓的切膚之痛——但使用的音樂手段卻極其精簡,旋律委婉,音色透明。這種獨一無二的悲愁詠嘆在他晚年的《大地之歌》與《第九交響曲》中達至完美,也成為馬勒“向死而生”的藝術的最終歸途。《大地之歌》尤其借中國唐詩意境,渲染出一派青春不在、對酒當歌、秋風蕭瑟、人去樓空的沉郁景象。最后的末樂章《送別》是馬勒一生音樂追求的集大成與制高點,“散文式”旋法的自如伸展與刺人心扉的音色處理相輔相成,在這里結出最甘美、最動人,同時也最令人酸楚的藝術之果。女低音歌者在全曲最后停留在“永遠(ewig)”一詞的反復沉吟中,樂隊中的鋼片琴聲響則輕輕飄過,晶瑩剔透。這是馬勒心目中的 “涅槃”意象,超越時空,無始無終……
接通傳統、現代與“后現代”
馬勒的音樂立意具有奇特的多維性。他的整體藝術觀念總體上屬于19世紀的“舊時代”,其諸多音樂表達也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風范。通過馬勒的個人努力,德奧音樂的兩大支柱性傳統——交響曲和藝術歌曲——不僅得到延續,而且發生重大轉型,并在內涵與形式上被予以雙重深化。
然而,深究起來,馬勒音樂中神經質的扭曲、病態的夸張以及神出鬼沒般的怪誕陰影直接指向了現代主義藝術中的表現主義。輩分上晚一代的勛伯格及其弟子(特別是貝爾格)曾親炙馬勒的教誨并受到鼓勵,最終將音樂推向現代主義的不歸路。而馬勒音樂的影子,一直回響在貝爾格、布里頓和肖斯塔科維奇等重磅現代作曲家的創作中。肖斯塔科維奇公開表白,馬勒是他最喜愛的作曲家。甚至可以說,沒有馬勒的指引,肖斯塔科維奇音樂中那種特殊的苦澀諷刺就不可能存在。
但馬勒的穿透力不僅如此。他已經成為音樂“后現代”癥候的預告者與指路牌。在經歷了20世紀的戰爭重創、意識形態對峙、核彈威脅、科技革命、環境破壞與價值瓦解的當前,馬勒的音樂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貼切地表達出人們生存體驗中的困惑、焦慮、彷徨和疑問,同時也因其本質上的浪漫主義遺韻,更激起了人類對逝去樂園和美好理想的眷戀與向往。
因此,馬勒的“復活”絕非偶然,更非暫時,他已經并將依然是“未來的同代人”。
(作者系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副院長)
相關內容
- 湯沐海 每一次音樂會我都酣暢淋漓2014-12-2
- 常思思:神曲不適合我,堅持走藝術高端路線2014-12-1
- 昆劇名宿林為林:突破自我再現大將軍韓信2014-12-1
- 裴艷玲正籌備新戲《漁夫恨》2014-11-27
- 捷杰耶夫:展現“老普”音樂的放肆之美2014-11-27
- 程學濤的演藝夢2014-11-27
熱點文章
樂器
日木
740)this.width=740"> 日木,羌族棰擊膜鳴樂器。又稱羊皮鼓。漢稱羌鈴鼓或羌族手鼓。流行于...
 名稱:中音在線
名稱:中音在線